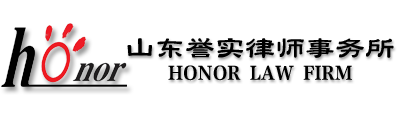2020年2月6日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下文简称“防控意见”)明确提出依法严惩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的犯罪,相较于2003年5月发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拒绝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的惩治意见,“防控意见”新增了“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但并没有重复“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的规定。
对于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的行为定性,关键在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及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分。在前述三个犯罪的多个不同点之间,罪过形态和危害客体是区分关键。
一、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罪过形态。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罪过形态争议较大。在故意说、过失说和混合过错说的争议中,笔者认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故意犯罪。首先,混合过错不成立。行为和结果的紧密联系决定了行为人对行为和结果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是一致的,对行为故意而对结果过失抑或对行为过失而对结果故意存在逻辑上的冲突,有违一般理性人的思维模式和社会经验。其次,法定刑幅度不能作为认定罪过的标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分别属于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同类客体的不同体现出社会危害性的差异。因此,即便法定刑相差较大,但并不能因此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解释为过失犯罪。我国刑法立法以故意犯罪为基本,过失犯罪必须法律有规定才构成犯罪。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没有明确规定为过失犯罪,也无“事故、不负责任”等过失犯罪的表述,因此,本罪属于故意犯罪。
罪过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主观心理状态。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罪过争议主要因为部分观点对刑法中的危害结果存在认识偏差。刑法中的危害结果是指行为对法益的损害和造成损害的危险。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客体是传染病防治管理制度,因此,本罪的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认识到自身的行为会危害传染病防治管理制度,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至于违反传染病防治管理制度之后的具体传播等危害结果,并不是本罪的认识内容,甲类传染病的传播以及传播严重危险属于本罪的客观超出要素。
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客体是传染病防治管理制度,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体是公共安全,由于甲类传染病传播的严重性,因此,危害传染病防治管理制度的行为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尽管如此,危害传染病防治管理制度的行为并不必然危害公共安全,两罪的差异在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管理制度的行为是否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过和行为内容。
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其认定关键不在于危害对象或者危害结果的数量多少,其在于危害对象和结果是否特定,也即危害和危险是否可控。这里的可控不是国家或者其他组织和他人对危害的可控性,是指行为人自身对于行为危害结果的可控。
如果妨害传染病防治管理制度的行为人对于传染病的传播是可控的,便认定该行为人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过和行为内容,其行为可能不能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妨害传染病防治管理制度的行为人对于传染病的传播是不可控的,便认定该行为人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过和行为内容,该行为有可能同时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根据想象竞合犯“择一重罪处罚”的原则,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该行为进行定罪处罚。
三、抗拒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具体认定。
抗拒意味着主观排斥,因此,抗拒疫情防控措施只能是故意,不存在过失的抗拒。应当区别抗拒疫情防控措施和过失未执行疫情防控措施。如果因过失未执行疫情防控措施,导致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危及公共安全的,应当认定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行为人因过失未执行疫情防控措施,也未导致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其不构成犯罪,应当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或者由有关部门予以其他行政处罚。
根据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的具体表现,如果行为人抗拒疫情防控措施,并能确保新型冠状病毒在特定范围内传播,且能够确保被其传染的人不再传染给其他不特定人群,也即其能够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进行有效控制,那么该行为并不危害公共安全。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属于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对于此种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的行为仅认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需要提醒的是:此处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的行为不包括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行为,如果行为人故意向特定他人传播新型冠状病毒,例如被确诊病人、病原携带者向特定他人吐口水,应当认定故意伤害罪。如果行为人对于自己的传播危害结果不能进行有效控制,或者虽然能确保自己在特定范围内传播新型冠状病毒,但被传染人可能向不特定他人传播的,应当认定该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是不可控的,仍然认为该行为人抗拒疫情防控的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此种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的行为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定罪处罚。
四、根本标准还在于是否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过和行为内容。
根据一般理性人的观点,被确诊病人、病原携带者或者被医疗机构疑似感染的行为人,其存在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概率较高,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行为可以认定其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和主观罪过,因此可以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但是,进入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并不是划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直接标准。根本标准还在于是否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过和行为内容。因此,被确诊病人、病原携带者或者被医疗机构疑似感染的行为人抗拒疫情防控措施,即便进入公共场所,但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过和客观可能性的,不应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被确诊病人、病原携带者或者被医疗机构疑似感染的行为人,抗拒隔离治疗,并未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仅在家里进行自我隔离。但如果其家人未进行隔离,家人的随意外出很可能导致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因此,尽管该行为人未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交通工具,但是其并不能有效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其对于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的行为具有了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内容和罪过,因此,此种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的行为应当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学院 聂慧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