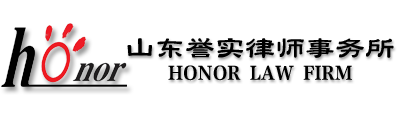从近年纠正的冤错案件看,证据和证明问题最易成为刑事审判中的“滑铁卢”。一些刑事案件的客观直接证据相对薄弱,有的主要依靠被告人供述(口供)和间接证据定案,此时如何审查口供至关重要。口供天然具有易变性和不可靠性,出于各种原因,被告人逃避制裁、被迫认罪、包揽罪责等情形均不鲜见。实践中,一种常见方法就是从“亲历性事实”判断口供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其广泛存在于庭审质证、法官心证和裁判文书之中,如认定某事实系被告人“非亲历不能知晓(描述)”。
“亲历性事实”的价值和类型
“亲历性事实”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亲身经历的犯罪事实和体验,尤其是外人不得知、侦查机关未掌握的那部分,有助裁判者判断真伪。“亲历性事实”的审查是贯彻自由心证原则的体现,具有两方面功能:一是验证性功能,裁判者通过一些细节验证口供的真实可靠性,确证案件事实;二是补强性功能,当根据口供提取到客观性、隐蔽性证据时,可以对口供进行印证或补强,提高司法证明的完成度。从证明方向看,“亲历性事实”有证实和证伪两种价值,类似于日本学者所提“秘密的暴露”和“无知的暴露”,前者指真凶在交代自己的体验与记忆的自白中,包含着令事实浮出水面的某些内容;后者即无辜者被迫供述时显现出的“非犯罪体验者”的想象性讲述。在日本刑事诉讼法中,判断“自白”证明力的标准之一就是自白是否符合客观事实的要素,包括是否“揭露秘密”。可见,“亲历性事实”的审查并非地方性经验,而是反映了共通的司法认知规律。
从刑事司法实践看,“亲历性事实”包括以下情形:一是先供后证的客观性证据和隐蔽性证据,如被告人供述的埋尸地点、财物和作案工具去向等,并据此提取到相关物证、书证。二是犯罪时间、地点、行为和对象中的隐秘性细节,如某强奸杀人案中,被告人供述先打算将被害人抛尸到甲化粪池,但盖板太重,移动未果,乙化粪池盖板较小较轻,遂抛尸到乙化粪池,后与侦查人员称重一致。三是与案件本身无关但可验证的事件和信息,如某故意杀人案被告人供述藏身被害人家阁楼,听见邻居来吃饭聊天,与证人证言印证;某交通肇事案被告人供述撞人后往左避让的细节,与监控视频印证。四是作为犯罪亲身经历者的实感和体验,如前述强奸杀人案中,被告人在讯问中模拟了性侵被害人的动作,还供述抛尸时将被害人头朝后扛在肩上,被害人的肚子贴着他,他明显感受到还有微弱的呼吸。以上均属于犯罪人独知的事实或特有的体验,不为外人所知,在历史真实与法律事实之间建立起了联结点,强化了证据的质量和数量,对于个案证明具有较高价值。
“亲历性事实”的误判风险
“亲历性事实”本质上属于经验法则的范畴,有赖于裁判者的经验知识,其最大风险就是以个人经验主观擅断口供证明力,先入为主进行有罪推定;以口供审查替代全案证据审查,降低证明标准,引发冤错案件。实践中应当防范三种误区。
一是侧重“秘密的揭露”,忽视“无知的暴露”。在层层推进的线型刑事诉讼构造下,侦、诉、审协作配合有余但制约不足,有罪思维定势和积极追诉的惯性比较明显。表现在“亲历性事实”判断中,就是以证实为主,证伪功能发挥不够。如福建缪新华案中,虽有被告人供述(后翻供)、勘验笔录和作案工具等证据,但对于侦查机关未掌握的分尸地点、被害人佩戴首饰去向等情况,被告人供述不清、缺乏细节,口供与其他证据未形成印证。遇到此类案件,要认真分析究竟是犯罪人逃罪的伎俩,还是无辜者“无知的暴露”,结合其他证据审查能否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二是倾向选择性认定,忽视全面性审查。许多冤错案件表面上看证据数量充分、供证一致,但只要仔细甄别,就能发现口供中有无法排除的矛盾,或者不利于定罪的反证或疑点,若对此视而不见甚至蓄意掩盖,就会误判案件事实。如聂树斌供述的作案地点、藏衣地点、尸体上的白背心、颈部花上衣、自行车位置等,与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内容基本一致,但以上供证一致是先证后供的结果,对判断口供证明力价值不高;同时,聂树斌对作案动机、被害人年龄、衣着、体态等事实细节供述前后矛盾、反复不定,无法与其他证据印证。
三是注重口供的经验判断,忽视客观证据收集。有的案件因年代久远等原因客观证据比较薄弱,通过审查“亲历性事实”形成心证、补齐证据链条实为无奈之举。但有的案件则是受“重口供、轻证据”理念支配,侦查机关将重心放在突破口供上,怠于收集客观证据,造成证据规则的失守。实践证明,现有的口供生产机制仍无法保障口供的自愿性和真实性。对口供的过分倚重和对个人经验的盲目自信,导致错失调取关键物证的时机,酿成冤错案件。
“亲历性事实”的审查方法
从实践看,“亲历性事实”的审查存在认识不一致、规则不统一等问题。为了防止“无真实性担保”的口供“长驱直入法官的心证”,助长司法擅断,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审查是否存在非法取证及供证关系。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是口供真实可信的前提,非法取证方法之下,口供的真实性往往难以保障。因此,裁判者仅静态审查案卷笔录是不够的,还要动态审查口供的形成过程,包括是否存在逼供、威胁、指供、诱供,指认、辨认工作是否规范,同步录音录像是否全面记录,口供是否随证而变等。如浙江张氏叔侄案中,张辉原本不知道“留泗路”,但“狱侦耳目”在指认现场前向其提示了抛尸地点,张辉遂根据路牌标识指认了抛尸现场。如果孤立、静态地看,认为张辉指认出留泗路属于非亲历不可知,就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此外,还要审查口供与其他证据的时间先后和逻辑关系,先供后证的价值一般大于先证后供,因后者存在侦查机关根据起获的证据逼供、诱供的风险。有的案件中,裁判者根据被告人供述与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等一致,认定被告人不亲历不可知,但由于负责审讯和现场的侦查人员可能进行信息交换,如不能排除逼供、诱供的信息源,则上述“亲历性事实”和供证一致的价值就会打折扣,尤其在客观证据薄弱的案件中,定性时应当谨慎。
二是审查口供内容是否符合逻辑与经验。裁判者运用的逻辑与经验应当是日常的、普遍的而非罕见的、个别的,口供蕴含的案件信息应当是有细节的而非泛泛的,供述的因果进程应当是自然的、合理的而非异常的,如果明显不符常情常理,严重偏离一般社会认知,则应当警惕。如聂树斌案中的关键物证花上衣,再审判决指出,证据显示聂家当时经济条件较好,衬衣就有多件,无证据证明聂有过偷盗劣迹,也无证据表明其对女士衣物感兴趣,而涉案上衣是一件长仅61.5厘米且破口缝补的女式花上衣,不适合聂穿着,故聂供述偷拿自穿不合常理。
三是酌情考虑情态辅助审查口供。“情态,谓表见于行为之情状。”我国古代有“五听断狱法”,现代证据制度中也有“以人之态度为证据方法”,如“人之表情、举止、手势、眼色、语调、羞忿、惊惶、踌躇、动静及其他精神异常等”,虽然情态不是法定证据类型,但情态与口供相伴生,实践中主要辅助判断口供真伪和发现真实。如前述强奸杀人案中,被告人指认现场时供述:“睡不着,怕她(被害人)窗子里面伸手进来。”同步录音录像显示在讯问的间隙,被告人叹气自语:“就是有点后悔也太晚了。”由于不存在外在压力,以上情态可以辅助审查口供的证明力。应当注意,“情态证据”虽有心理科学和神经生物科学依据,但因主观性太强,无法规范和量化,可能加剧司法偏见,将案件引入歧途。如呼格吉勒图案中,被告人刚成年且涉世未深,在主动报案时因害怕而精神紧张本属正常,但办案人员却据此认为他有犯罪嫌疑。故而此种方法必须慎之又慎、严格适用,更不应作为单独的证据使用。
四是审查口供是否与其他证据印证。“亲历性事实”的审查属于口供范畴,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定案,而不应孤立考量;即便认为口供证明力较高,也不能取代全案证据审查,应遵循“孤证不能定案”原则,并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口供即使看上去再可信,也应能够与其他证据印证,且所有证据指向一致,没有无法排除的矛盾。
道者术之源,术者道之表。“亲历性事实”虽然是一个实践性、技术性问题,但审查判断过程体现了裁判者的智识、理性和经验,反映了无罪推定、证据裁判、人权保障等理念,用之得当可谓明察秋毫,用之不当则存在冤错隐患。“刑操生死,法执衡权”,裁判者不可不慎。
(作者单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汤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