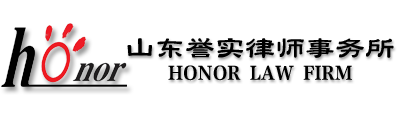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规定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以有效规制与违法犯罪相关的设立网站、通讯群组和发布信息行为。然而,实践中该罪却长期“遇冷”,未能充分实现预期目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解释》)就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适用作出规定,对于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引作用。此后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适用日渐增多,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与相关犯罪未能有效区分,导致实践存在一定的分歧。有必要立足刑事规范进行精准区分,以确保该罪的依法适用。
一、与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区分
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规定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与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二者均指向违法犯罪信息,且均可能由网络服务提供者实施,实践中也对如何选择和适用两罪存在一定的模糊认识。可重点考虑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区分两罪:
第一,网络服务性质不同。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主体已在刑法中明确规定,即“网络服务提供者”。同时,根据《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解释》第一条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包括提供“信息发布”“即时通讯”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未明确规定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主体,根据关于非法利用信息网络行为的规定可以认为主体包括两类,即网站、通讯群组的设立者和违法犯罪信息的发布者。可以看出,仅从形式上进行考察,两罪主体确实存在交叉。因此,为有效进行区分,司法实践中应依据网络服务是否具有合法性在实质上进行把握,即明确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涉及的“网络服务”具有合法性,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涉及的“网络服务”不具有合法性。例如,行为人如果合法提供发送短信服务,但是该服务被他人利用发送违法犯罪信息,而其未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且拒不改正,则考虑是否构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如果行为人系为了违法犯罪活动发送短信,则考虑是否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第二,犯罪行为类型不同。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行为类型系不作为,即负有法律上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但是未履行该义务;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行为类型系作为,即实施非法设立网站、通讯群组或者发送信息的行为。实践中可重点把握行为人和相关他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对他人的行为、信息具有管理职责,但未实际履行且拒不改正,则考虑是否构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如果参与、帮助他人实施违法犯罪,非法设立网站、通讯群组或者发送信息,则考虑是否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第三,违反的法律规范不同。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系违反强制性规范,即“应为而不为”。行为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但未实际履行;经监管部门责令必须“采取改正措施”,但拒不改正。与之不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系违反禁止性规范,即“不应为而为之”。本身设立网站、通讯群组或者发送信息的行为既可能合法也可能非法,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强调行为的“非法”,该罪所规制的是非法实施上述行为的情形。
二、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区分
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同样具有关联性,二者均一定程度上参与他人的违法犯罪活动。近年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数量呈现“井喷”态势,已成为各类刑事犯罪中排名第三的罪名,两罪的竞合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特别是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等关联犯罪的发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等司法文件明确将两罪作为其他信息网络犯罪的关联犯罪,在此背景下更需厘清二者的实质区别。可重点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判断:
第一,与关联行为关系的区别。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提及了“违法犯罪活动”,第(二)项提及了“违法犯罪信息”,即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关联行为既可以是违法行为,也可以是犯罪行为。与之不同,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第一款明确采用“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和“为其犯罪提供”的表述,即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关联行为仅限于犯罪行为。《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解释》第七条进一步明确,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规定的“违法犯罪”,包括犯罪行为和属于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类型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
从实践来看,不少非法利用信息网络行为与多起违法犯罪行为关联,如“两高”公布《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解释》时一并发布了两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犯罪典型案例。在黄杰明、陶胜新等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中,被告人黄杰明使用昵称为“刀剑阁”的微信,在朋友圈发布其拍摄的管制刀具图片、视频和文字信息合计12322条。在谭张羽、张源等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中,两被告人从事为他人发送“刷单获取佣金”的诈骗信息业务,并且有专人招揽、联系有发送诈骗信息需求的上家、接收上家支付的费用及带领其他人发送诈骗信息。在此意义上,非法利用信息网络行为与“违法犯罪”行为的关系,某种程度类似于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组织卖淫行为与卖淫行为的关系,其关联行为至少具有行政违法性,但是行为本身具有刑事违法性。在实践中,应特别关注为大量违法犯罪行为搭建平台、批量提供服务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行为,依法予以打击。
第二,行为所涉人员范围的区别。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仅强调设立网站、通讯群组或者发布信息需要与“违法犯罪”关联,因此无论是为自己或是他人的“违法犯罪”实施上述行为,均可成立该罪。与之不同,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明确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其他帮助,因此仅可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实施帮助行为。
第三,行为方式的区别。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行为方式包括两种,即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以及发布违法犯罪信息或为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均属于信息通讯层面。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行为方式包括提供技术支持和其他帮助,类型十分广泛,可以涵盖各类帮助行为。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提供设立网站、通讯群组或者发布信息这样的信息通讯帮助,能否同时符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通讯传输”这一技术支持方式。从刑法的体系适用和两罪司法实践来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通讯传输”通常指提供GOIP电话、VPN虚拟专用网络服务等建立用户之间传输通道的行为,不包括设立网站、通讯群组或者发布信息行为,明确这一点对于避免两罪行为认定的交叉具有重要意义。
三、与关联犯罪的区分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是我国基于网络犯罪产业链的时代发展所设立的创新性罪名之一。不少学者基于传统刑法理论将该罪解读为“预备行为实行化”,但是如果关联的“实行”行为仅是“违法活动”,则提供信息通讯帮助的所谓“预备”行为则缺乏入罪的根本性前提。而且,从刑法总、分则规定和刑法理论来看,即便是为诈骗犯罪等目的“发布信息”等行为已经实际着手实施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也规定大量发送诈骗信息或拨打诈骗电话的行为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因此,司法实践应回归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犯罪的本质,探索和发展契合我国网络犯罪治理实践的审判理论。可立足独立性、关联性并存的视角,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诈骗、赌博、毒品等关联犯罪的区分:
第一,非法利用信息网络行为具有独立性。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规定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系情节犯,只要符合该条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要求,即可依法予以处罚,无须依托关联犯罪进行刑事评价。而且如前所述,非法利用信息网络行为可能系为大量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信息通讯帮助,只要符合《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解释》第十条规定的标准,即可依法予以处罚。
实践中,非法利用信息网络行为的独立性还体现在行为人往往不参与具体的关联犯罪。如全国法院2019年十大毒品(涉毒)犯罪典型案例之一,梁力元非法利用信息网络、非法持有毒品、汪庆贩卖毒品案中,被告人梁力元架设并管理维护视频网络平台,“以虚拟房间形式组织大量吸毒人员一起视频吸毒”,仅是“间接促成线下毒品交易”。该案中,被告人归根到底由于(非法)网络平台地位承担刑事责任,并非由于向关联犯罪提供具体的帮助。
第二,主观认识的要求与关联犯罪不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在主观方面要求认识到违法性,但并不具体要求认识到刑事违法性。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仅要求行为人认识到所设立的网站、通讯群组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或者为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该款第(二)项仅要求行为人认识到所发布的信息系“违法犯罪信息”。与之不同,关联犯罪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其所实施的行为被刑法禁止,并且认识到具体的犯罪行为类型。
这一区别也有利于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更好发挥严密刑事法网的作用。比如一些未列入“毒品”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区分该类药品的使用目的作出区分规定,如果行为人出于非医疗目的,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贩卖该类药品的,按照贩卖毒品罪认定处罚;如果行为人出于医疗目的,非法贩卖该类药品,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依此认定处罚。但实践中出现了不少并非基于吸食用途、医疗目的,而是为他人实施强奸、盗窃等违法犯罪活动通过网络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案件,对其难以按照前述规则处罚。就此情形,只要行为人认识到网站、通讯群组或信息指向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系“违禁物品、管制物品”,即可按照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处罚。
第三,刑事处罚区别于关联犯罪。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刑罚区间,即“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处罚相对较轻。与之不同,关联犯罪的处罚则可能十分严厉。例如依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最高可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再如依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这充分说明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主要聚焦打击网络犯罪产业链中的信息通讯参与环节,司法实践应充分考虑其与关联犯罪处罚的区别,并活用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第三款“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寻求最佳的适用效果。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王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