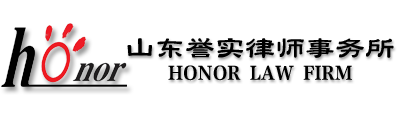通说观点认为成立盗窃罪要求秘密窃取,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实务的普遍认同。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盗窃罪是秘密窃取。从“窃”一词的本来含义看,就具有“秘密性”,如“窃窃私语”“窃以为”这类在公众心中已经达成共识的语言用法。古代刑法区分“窃盗”与“强盗”,就表明前者是秘密的,也就是盗窃罪,后者是公开的,也就是现今的抢劫罪。理论上有学者主张盗窃可以是公开的,认为当着被害人的面取走被害人的财物,也应认定为盗窃罪,并提出了“公开盗窃”这一既公开、又秘密的概念。这一观点扩张了盗窃罪的范围,也就当然地限缩了抢夺罪的成立范围,认为成立抢夺罪需要对物使用暴力、夺取被害人紧密占有的财物。公开盗窃论的观点与我国司法实践及理论通说存在一定差异,其理论适用仍需结合实务与体系逻辑进一步探讨。
一、盗窃是否包括公开不能完全参照德日刑法学
德日刑法中的盗窃罪既可以是秘密的,也可以是公开的。但是,德日刑法中是没有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抢夺罪,我国刑法中有盗窃罪、抢夺罪、抢劫罪,而德日刑法中仅有盗窃罪、抢劫罪。我国刑法中的抢夺罪必然在德日刑法中被“分流”至盗窃罪、抢劫罪:以行为是否可能会侵犯人身权利为标准区分盗窃罪与抢劫罪,如果行为没有侵犯人身权利的可能,无论是秘密还是公开,都构成盗窃罪,而对物使用暴力夺取被害人紧密占有的财物、行为有侵犯人身权利的可能性则被认定为抢劫罪。考虑到德日刑法中盗窃罪与抢劫罪的法定刑差异较大,对于以公开、和平方式获取他人财物,认定为更轻的盗窃罪,也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而我国刑法中在盗窃罪与抢劫罪之间还存在抢夺罪,就不宜完全参照德日刑法中盗窃罪的概念。我国刑法中的抢夺罪应该是承载了限缩盗窃罪与抢劫罪的范围的功能。抢劫罪是一种复合行为犯,既侵犯人身权利也侵犯财产权利。但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对被害人人身权利侵犯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或者行为本身相对单一,即使造成了被害人伤亡结果的,也仅能认定为是抢夺罪。例如,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抢夺罪的加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就包括了抢夺致人重伤、死亡的结果。对物使用暴力也并非抢夺罪独有的特征,如果对物使用暴力时侵犯人身权利的可能性较大,应认定为抢劫罪。前述2013年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驾驶机动车、非机动车夺取他人财物,明知会致人伤亡仍然强行夺取并放任造成财物持有人轻伤以上后果的,应当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此外,抢夺罪也会“挤占”盗窃罪的部分空间,我国刑法中盗窃罪的范围就不可能像德日刑法中的那样宽泛。较之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公然夺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无论是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还是从社会一般公众的认识来看,危害性都大于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因此,我国刑法中的抢夺罪是危害性大于盗窃罪、小于抢劫罪的部分行为的“集合”。
财产犯罪是一种古老型犯罪,与特定的社会文化、公众观念是密切相关的,虽然不同国家的财产犯罪有其共通的原理,但亦具各国的特色。包括各国财产犯罪的罪名数量、具体个罪的构成要件、此罪与彼罪的区分等,均呈现出诸多不同与特色。以抢劫罪为例,我国刑法中的抢劫罪所规定的法定刑相对比其他国家如德国、日本的更重,并且我国刑法中的寻衅滋事罪、抢夺罪也“分流”了其他国家刑法中抢劫罪的部分范围。因此,虽然我国刑法理论认为抢劫罪的手段行为要求足以压制被害人的反抗,但实务中诸多判决进一步强调,只有暴力手段有可能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才能成立抢劫罪。值得注意的是,凡是立法上没有规定抢夺罪的国家,多认为盗窃罪既可以是秘密的,也可以是公开的。但是,规定了抢夺罪的国家,则强调盗窃罪必须是秘密窃取,如俄罗斯、越南、泰国、蒙古、朝鲜等。例如,《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第158条规定:“偷窃,即秘密窃取他人财产。”第161条规定:“抢夺,即公开夺取他人财产的行为。”
二、以秘密与公开区分盗窃罪与抢夺罪具有合理性
首先,公然夺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认定为抢夺罪更符合国民的既有的“明抢暗偷”的观念,认定为盗窃罪会冲击公众的既有认知。如果将秘密与公开均认定为盗窃罪的行为方式,就相当于将“秘密”与“公开”等同视之而均认定为盗窃罪,有违罪刑均衡,也易导致盗窃罪构成要件缺乏明确性、类型性。我国刑法对于其他犯罪的规定,也多将“公然”“公开”的行为方式与“非公开”的方式另行区别对待,例如,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刑法对其规定了加重的法定刑。刑法中的其他相关罪名的认定也是坚持了“抢”是公开的,例如,刑法中的聚众哄抢罪,也并没有要求“哄抢”必须是对物使用暴力、夺取被害人紧密占有的财物,只要是公开的方式即可。
其次,持公开盗窃的论者批评“秘密窃取说”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如何认定秘密性存在模糊,认为盗窃罪的秘密性已经被实务所抛弃。通说观点认为,行为人主观上认为是秘密,但客观上是有人知晓的,也是秘密窃取,但这并不意味着盗窃罪的秘密性已经被抛弃。盗窃罪之所以要求“秘密性”,在于行为人主观上不想让被害人知晓,趁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取走财物。例如,甲在路边假装车主的样子,利用万能钥匙打开停在路边的自行车,事实上,车主及其好友均在远处目睹了甲的这一行为,而甲对此并不知情。甲主观上认为是秘密的,但事实上是公开的、被他人知晓的,这种行为仍然被认定为是秘密窃取而构成盗窃罪。
持盗窃可以是公开的论者认为,既然客观上是已经被他人知晓,又何谈秘密,进而否认盗窃罪要求秘密窃取。笔者认为,这样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主观认识与客观现状存在偏差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例如,行为人主观上想杀人并基于此而开枪,但客观上被害人并不存在的,也可以认定是故意杀人罪。行为人主观上想贩卖毒品,客观上误将面粉当成毒品而贩卖的,也应该成立贩卖毒品罪。这绝不是主观归罪,更不能据此认为,客观上没有人也可以成立故意杀人罪,就否认故意杀人罪的对象是人,客观上没有毒品也可以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就否认贩卖毒品罪的对象是毒品。也不能认为客观上是公开的,就否认盗窃罪的秘密性。
三、以是否对物使用暴力区分盗窃罪与抢夺罪更具不确定性
盗窃罪的秘密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表现形式也多样化,行为人主观上认为的秘密性在客观上可能并不“秘密”。随着摄像监控的普及,诸多盗窃行为可能会被被害人知晓,或者说,对被害人而言是公开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需要重构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而认为盗窃就可以是公开的。只是对于盗窃罪秘密性的认定,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存在偏差的现象会逐步变多。
以盗窃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为例。早期商品经济不够发达,商品的种类、价格相对单一,行为人对商品价格的认识不会出现明显的偏差,主观与客观是较为一致的,实务中也多以盗窃对象的实际价格来计算犯罪数额。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同一类型的商品,价格差异可能很大,完全可能出现行为人主观上认为所盗窃的手表价值数额较大,但客观上手表价值数额特别巨大,这种情形仍然需要尊重行为人的主观而认定为盗窃数额较大而非盗窃数额特别巨大。同样,行为人主观上想秘密窃取,客观上是公开的,认定为盗窃罪的理由也是秘密窃取,而非公然夺取。
以是否对物使用暴力而夺取被害人紧密占有的财物,作为区分盗窃罪与抢夺罪的标准,较之秘密与公开的区分标准,标准并非更明确。所谓的成立抢夺罪要求“对物使用暴力”必然面临着暴力的程度的界定,进而合理划分与盗窃罪、抢劫罪的界限。我国刑法中其他犯罪涉及手段行为是暴力的,同样面临着判断上的不确定性,比如,实践中,对于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之所以存在判断上的反复与不确定性,很大原因是暴力的程度如何划定。此外,以被害人是否“紧密占有”财物来区分盗窃罪与抢夺罪,如何判断是否“紧密”更是存在不确定性。
以对物使用暴力作为区分盗窃罪与抢夺罪的标准,其标准的合理性也值得商榷。如果贯彻此种标准,盗窃罪的范围将被扩大化,既包括秘密方式,也包括公然的方式,两种方式的危害性是否相当也是值得商榷的。我国刑法中抢劫罪的手段行为包括暴力、胁迫以及其他方法,既然使用暴力之外的胁迫、其他方法的都能够被认定为抢劫罪,那么,对物使用暴力,夺取被害人紧密占有的财物,且具有造成被害人伤亡的可能性却被认定为更轻的抢夺罪,并不合理。对物使用暴力的前提是要求被害人紧密占有财物,那么,这种暴力很可能甚至必然侵犯人身,这也容易混淆抢夺罪与抢劫罪。
四、突破盗窃罪的秘密性的理论创新应慎重
一种创新的理论从其提出到能否被实践所采纳,可能是较为长期且反复的过程,并非当然正确。盗窃可以是公开的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至今,依然没有得到实务的支持,需要重新审视该理论在我国当下的合理性。笔者并非刻意维护通说关于盗窃罪的秘密性,只是认为,当某一种理论在实践中普遍适用且没有明显困惑的情形下,移植域外理论就需要慎重。当被害人的面公然取得其财物的案件是一直存在的,认定为抢夺罪也并没有引发异议且得到了公众的普遍认同。突破盗窃罪的秘密性还会打破我们既有的观念,甚至打破我们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将“明抢暗偷”修正为是“公开地偷”,其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值得思考。
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借鉴域外的理论与立法,但作为传统型犯罪的财产犯罪,各国立法、司法与理论的背后更是其文化、观念的体现,对财产犯罪理论与立法的修正不能忽略这一现实。理论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刑法学研究在合理借鉴域外经验的同时,要摆脱对域外刑法教义学的过度路径依赖。刑法教义学上的理论移植并非像自然科学领域的技术引进那么便捷,国民观念、文化传统、语言习惯、政治与法律制度等,都是必须考量的因素。坚持盗窃罪的秘密性,无论从我国国民观念的认同度,还是从司法实践的效果来看,在当前都是更为务实的选择。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人工智能法学院 郭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