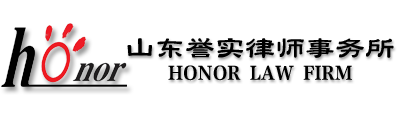【出处】《中外法学》2008年第1期
【写作年份】2008年
【正文】
全球化,尤其是资本市场、公司控制权市场的自由化,使得公司治理上产生了强烈的进化趋同压力。汉斯曼和卡拉克曼教授坚定地宣布“股东导向的模式”(shareholder oriented model)已经成为进化趋同(convergence)的主导模式。他们将其动力界定为其他竞争模式的失败,学界的共识。 但究其核心,仍然是一种基于市场竞争推动法律演进的进化理论。来自于资本、产品、要素和劳动力市场的压力,迫使以利益攸关者为导向的模式(stakeholder models)的重要性下降。在资本市场主导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只有更好地对股东利益加以确认和保护,通过诚信义务(fiduciary duty)来约束代理人的利己和机会主义行为,并且通过明晰的合同保护和机制设计来确定其他主体的权利,才能更有效地满足市场的扩展。
进化理论本质上是法律的竞争理论(law’s competition),与之相关的是规制竞争(regulatory competition)理论。进化理论是如此的有力,它刻画了公司法的历史。不同的法律规则系统之间出于对资本、就业、税收等原因的竞争而不断地优化和改进规则,导致了对规制放松(deregulation)的进程。英国和荷兰之间的竞争,导致了1600年和1602年的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的出现和制度创新,并导致后者被大陆法学者看成是现代公司制度的滥觞。 英国在19世纪初期学习大陆法上的康枚达(commenda),引入了有限合伙, 1822年美国也学习了这一制度。1811年,纽约州最早规定,在特定的制造业中,公司的资本总额不超过10万美元时,所有的申请人都受到有限责任的保护。 英国在1855年学习了这一制度,向所有的公司股东提供有限责任的保护,从而被视为真正的商事公司法的开始。公司法的形成如此,变化也是如此。德国对有限责任公司的创造,美国从新泽西州到特拉华州的公司法的自由化,有限责任合伙(LLP)和有限责任公司(LLC)在全球的扩展,以至于最近日本废除大陆法上的有限责任公司,采纳美国的LLC制度。
尽管存在着对特拉华州现象的争议,比如是否其领先地位是由于竞争造成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尤其是从公司法的整个进化历史来看,竞争的压力的确是法律移植和模仿的动力。国与国之间,州与州之间的竞争,推动了公司法更为自由、更为合理的发展趋势,是进化理论的一个强而有力的支持点。乃至于在1930年代,以美国示范公司法为典型,完成了向现代的“授权式”(enabling)、“许可式”(Permissive)以及“自由式”(liberal)的公司法的转型。 由于受到了来自于市场的压力,故而公司法中所带有的强行性规范不断发生变化,从事前的规制、审查、限制越来越向事后的司法裁量转化。这不仅促使了许多对公司行为的规制、目的限制、资本审查不断放松,甚至也在创造着基本种类的转换。
进化理论中的理想公司类型和治理结构,是股东导向的公司治理模式。而LLSV的研究为这种理想模式提供了实证支持。他们最早采用49个现在已经扩大到150多个国家的数据,按照法律输出和移植形成的法系概念,得到了较为明确的结论。他们将这些国家公司法(也包括相关的证券、破产)中所确立的制度,以各国的资本市场发展程度来衡量,判断哪一个法律体系能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结果表明,在四大法律体系之中,英美法对投资者、债权人的保护最好,其资本市场也最发达;斯堪的纳维亚法系次之,德国法又次之,法国法最差。 尽管这种实证研究还存在着很多争议和批评, 但总体上来说,LLSV的研究为我们判断公司法在促进经济效率目标上提供了一个判断尺度。
后进国家,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主动进行变法的继受法国家,在以外国法作为规则吸收和引入的正当性的时候,尤其是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的改革思想路线下,为什么不能在历次的公司法规则的形成以及规则的修订之中,向最为有效率的、至少是论证最好的模式转轨呢?为什么不能向最强者学习呢?
既有的法律规则可能会有效率上的优势,因为制度和结构可能已经考虑了在这些规则下的需求和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替换另一种规则,可能会导致已有的制度和职业上的基础设施变得荒废、不相称,并要求新的投资。众多的博弈者——管理者、所有者、法律人、会计人员等等,已经在人力资本上做出了投资,操作模式上也已经使用了既有的公司法规则。而替换公司法规则可能会要求这些博弈者来作出新的投资并采用新的规则。
公司法的规则由于和财产法、合同法、证券法等其他法律体系的嵌入关系,并且和司法系统、法官的思维习惯等等制度实施体系融合在一起,故而在转轨的时候产生了成本,从而导致了先前的选择制约着此后的选择。沿着这一框架和命题,欧洲学者也对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进行了分析。
路径依赖的概念来源于系统论,和混沌理论(chaos)相关。路径依赖导致转轨的困难,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决策在时间序列上作出,导致的顺序决策关系。 除了两位公司法学者外,法律经济学学者区分了三种不同层次的路径依赖, 其原因、结果和表现并不相同。第一级路径依赖,也称之为起点敏感的路径依赖。初始条件不同,导致可能在存在着多个最优,某种路径依赖选择了某一种。这并不意味着无效率;第二级路径依赖,是由于信息或者知识不完备而导致的。这包括对起始条件的敏感,也包括改变结果的成本昂贵,并且会不断繁衍错误;第三级路径依赖,是由于结构性错误,而被锁定在特定的坏的均衡之中,并且这种错误结构日益产生更强的需要,从而导致无效率。第一级路径依赖是时间内的关系(intertemporal relationship);第二级是在时间关系内繁殖(propagate)错误;第三级不仅仅繁殖了错误,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无效率。罗伊在对法律中的路径依赖提出了三种强度上的划分。 与之类似,他区分为弱的、中度的和强的三种路径依赖。
在公司治理上,最近似于现行的中国大陆的,可能是台湾地区的公司法,后者沿袭了民国时期的公司制度传统,而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框架则基本上抄袭自大清商律。大清商律中的公司律基本上照搬照抄了日本的立法。按照一些夸张的说法,早期日本商法中的公司部分吸收了英美法和大陆法的优点,其中的比例为2:3。 这种评价显然是错误的。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从今天中国的公司治理中,看到当时所沉淀下来的基础性结构:以股东权力为中心,三角形的公司治理的基础结构,对注册资本的限制、审查和复核构成了对公司规制的主要途径,以物权的方法来处理公司和股东之间的财产权利分配。这些基本特点并没有实质上的变化,只是在这种规制方法或者结构上,进行量的调整而已。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所学习的西方商法,在整个世界的公司法历史之中,处于并没有进化到现代公司法的阶段。前面提到1811年纽约州和1855年英国的有限责任法一般被视为是商事公司法的开始。尽管法国从拿破仑商法典的时候已经规定了股份公司,但法国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公司法,并不是拿破仑商法典,因为该法典中的股份公司仍然是特许公司,非常严格和稀少。法国学者自以为是1867年的版本。 而德国法在1900年的时候才创造了有限责任公司。在这期间,日本和中国所学习、移植的公司制度,是在各国当今主流的公司治理尚未出现时候的模式。毫不夸张地说,在日本和中国学习的一刹那,公司治理在大陆法上都是荷兰模式,即荷兰东印度公司所确立的公司治理模式。这是中国的三角形公司治理结构的来源。而德国法上的共同决策机制是20世纪中期确立,主银行制度等则是在20世纪初期浮现定型的。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以注册资本来规制公司财产,公司目的的严格限制,依赖于公司登记制度等,这被称之为规制的(regulatory)、家长作风(paternalistic)的公司法。而以授权性规范为主,关注诚信义务,以公司融资和管理层控制公司为主要核心规范,建立在比较彻底的两权分离上的现代公司法,被公认为是在1930年代定型的。 毫无疑问,中国第一次学习的公司法是在进化体系中尚未定型的公司法。
自1908年清末变法之后,中国法律体系的进化由于政治上、经济上的与世界隔离,更多地吸收了苏联模式,进而通过政治一经济的官僚体系,将这一模式的内核延伸到了公司治理之中。本文的考察揭示出,中国公司法的特殊性并不是物种多样性的表现,并不和德国、日本的传统相同,而是一种进化不足的表现。这就意味着,尽管存在着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存在着股东利益保护和管理层谎报和偷懒(shrinking and sharking)之间的对立,存在着国有股和非国有股之间的市场分割而带来的对立,但是在公司法和公司治理上的核心问题,仍然是过度规制和市场自由之间的矛盾,也表现为事前的行政规制和事后的司法裁判之间的权衡(trade—off)问题。
究竟有没有可能跳出一个坏的均衡,有没有可能完成一个以授权为核心的公司法的进化?这也许不仅仅是一个公司法和公司治理的问题,而是整个法律制度乃至政府治理面临的同样问题。在有些学者看来,这一进程并不乐观。似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被锁定的均衡,如同罗伊所说的强度路径依赖,或者如法律经济学学者所说的,第三级的、不可避免的繁殖错误的路径依赖,而难以跳出。比如有学者存在着悲观的论调,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个从“采邑”到“宗法”的过程,不可能过渡到真正的市场。
【作者简介】
邓峰,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
See Henry Hansmann & Reinier Kraakman,The.End of History for Corporate Law,Georgetown Law Journal,Vol.89,2001,pp.439—468.
See M.Schmitthoff,The Origin of the Joint—Stock Company,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Vol.3,1939—1940,pp.74—96、93—94.
See Michael Lobban,Corporate Indentity and Limited Liability in France and England:1825—67,Anglo—American,Law Review,Vol.25,1996,pp.397—440.
See Maurice J.Dix,Adequate Risk Capital:The Consideration for the Benefit of Separate Incorporation,Northwest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53,1958—1959,pp.478—494、478,pp.479—480.
See James D.Cox and Thomas Lee Hazen,Cox & Hazen on Corporations:Including Unincorporated Forms of Doing Buisness,Znd ed.,Vol.1,New York:Aspen Publishers,p.91.
See Larry E.Ribstein,The Deregulation of Limited Liability and the Death of Partnership,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Quartely,1992,pp.417—475.
See 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and Robert Vishny.Law and Fin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6,1998,pp.1113—1155.
See John C.Coffee,The Future as History:The Prospects for Global Convergenc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t’s Implication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93,1999,pp.641—708.文献众多,兹不一一引述。
类似的争论也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出现,比如参见蒙那代里:“关于中国民法典编纂问题的提问与回答:以民法典的结构体例为中心”,《中外法学》2004年第6期。
Lucian Ayre Bebchuk and Mark J.Roe,A Theory of Path Dependence in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Governance,Stanford Law Review,Vol.52,1999,pp.128—170、156.
See Klaus Heine and Wolfgang Kerber,European Corporate Laws,Regulatory Competition and Path Dependence,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13,2002,pp.47—71.
See Stephen E.Gargolis and S.J.Liebowitz,Path Dependence,in Peter Newman,ed.,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and the Law,Macmillan Reference Limited,1998,Vol.P—Z,p.17.
See S.J.Liebowiz and Stephen E.Margolis,Path Dependence,Lock—in,and History,Journal of Law,Economics,& Organization,Vol.11,No.1,1995,pp.205—226.
Mark J.Roe,Chaos and Evolution in Law and Economics,Harvard Law Review,Vol.109,1996,pp.641—668.
参见民友社:《新商法(商人通则,公司条例)释义》,民友社1914年。
See Judah Adelson,The Early Evolution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in France,Business History Review,Vol.31,1957,pp.226—245.
See James D.Cox and Thomas Lee Hazen,Cox & Hazen on Corporations,Vol.1,New York:Aspen Publishers,2003,pp.90—91.
See Nicolas C.Hawson,Regulation of Companies with Publicly Listed Share Capital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38,2006,pp.237—249.
See Max Boisot and John Child,From Fiefs to Clans and Network Capitalism:Explaining China's Emerging Economic Order,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41,1996,pp.60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