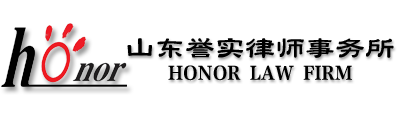| 关键词: 物权变动/区分原则/形式主义/物权行为/ 无权处分 |
| 内容提要: 区分原则不仅本身对于物权变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是对物权变动法律关系进行分析的重要思维工具。对区分原则的认识必须以其所处的物权变动模式为基础,我国《物权法》中所确立的是以债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为背景的区分原则。区分逻辑应该在有关物权变动的领域中得到贯彻,以无权处分为例,在将债权形式主义下的无权处分行为性质界定为债权合同的基础上,应该区分无权处分行为与物权变动结果,将无权处分行为一般认定为有效。 |
|
物权变动,作为一种权利的动态现象,从物权本身的角度说,是物权的发生、变更、消灭;从物权主体的角度说,是物权的取得、变更、丧失。 [1]我国《物权法》则将物权变动表述为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 [2]本文要讨论的区分原则不仅本身对于物权变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是对物权变动法律关系进行分析的重要思维逻辑基础,毫无疑问应该在有关领域中得到贯彻。因此,本文将在对区分原则特点进行探讨的基础之上,以物权变动中的无权处分为例,讨论区分逻辑在具体问题中的贯彻与运用。 一、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下的区分原则 对区分原则的认识必须以其所处的物权变动模式为基础。在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不动产或动产上的物权变动仅因当事人的债权合意而发生,登记或交付是对抗要件,债法上的效果和物权变动的效果系于同一法律行为发生,当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时债权行为也归于无效,因而并无区分原则存在的余地。而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法律构造则决定了其一定程度的区分的要求,如下文所述。
(一)形式主义变动模式下的两种区分原则
物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下,欲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除债权合意外,还须另有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以及履行登记或交付的法定形式。在此种立法例下,一个法律行为不能同时发生债权及物权变动之二重效果,债权行为只能生债之关系,必须另有物权行为,方能生物权变动之效果,故物权行为另独立存在,有独立性。 [3]因此,物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下的区分原则指的是物权变动的原因法律行为(债权行为)与直接发生物权变动效果的法律行为(物权行为)相区分,德国学者称之为“Trennungsgrundsatz”或“Trennungsprinzip”,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学者称之为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或分离原则。 债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下,除债权合意外,仅须履行登记或交付的法定形式,就可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在此种立法例下没有独立存在的物权行为,但仅存在有效的债权行为也并非物权变动的充分条件,物权变动效果的发生系于债权行为和公示的合力。公示行为本身是对债权行为的履行,是事实行为,不包含任何意思表示。因此,债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下的区分原则指的是作为物权变动的原因法律行为(债权行为)与履行该法律行为所发生的物权变动效果相区分。
在典型的物权行为理论中,物权行为除具有独立性外,还具有无因性,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的效力评价互不影响,即物权行为的不成立、无效、被撤销不影响债权行为的效力,债权行为的不成立、无效、被撤销也不影响物权行为的效力,因此物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下的区分是双向的区分。而在债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下,物权变动是有因的,物权变动的效果受制于原因行为的效力,当原因法律行为不成立、无效、被撤销的情况下物权变动也归于无效,因此该模式下的区分是单向的区分。
(二)我国民法中物权变动区分原则的性质
首先必须提及的是,孙宪忠教授在我国虽然较早地论述了区分原则,但在进行相关论述的时候实质上是将区分原则与分离原则(物权行为独立性) [4]的概念混同了。他在《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的区分原则》一文中对区分原则概念的表述虽然是债权形式主义的:“所谓区分原则,即在发生物权变动时,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物权的变动的结果作为两个法律事实,他们的成立生效依据不同的法律根据的原则。” [5]但他在《再谈物权行为理论》一文中却将物权行为独立性也称为区分原则, [6]而在《我国物权法中物权变动规则的法理评述》一文中,区分原则的基本内涵更是被直接解说为:“债权合同依据债的生效要件;而物权变动即处分行为的生效依据物权公示原则。” [7]无怪乎有研究物权行为理论的学者将孙宪忠教授关于区分原则的论述归于物权行为分离原则的各种观点之一。 [8]孙宪忠教授关于区分原则的论述的问题就在于,他的表述并未明确向我们揭示出其赖以区分的依据——物权变动模式所在,因此我们也就无法就区分原则下结果与原因二者效力之间的关系做出全面的推论。 [9]必须明确,区分原则是物权形式主义区分原则的上位概念,后者只是区分原则的一种,而不能等同于区分原则本身,否则不仅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也不利于研究的进行。 《物权法》第15条在我国法律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区分原则:“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从我国立法机关起草的每一稿《物权法(草案)》到最后正式颁布的《物权法》第9条第1款和第23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所确立的都是债权形式主义为原则的物权变动模式,可以说这是我国立法机关在立法时的本意。并且这也是我国司法机关在长期的实践中所形成的思维习惯和采纳的观点。 [10]因此从客观上来说,债权形式主义是我国《物权法》所确立的物权变动的一般形态,而我国《物权法》中的也是以债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为背景的区分原则。 二、债权形式主义下无权处分行为之界定
“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来源于德国民法。作为物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代表的德国民法中,在物权变动领域处分行为是指与债权行为相对应的物权行为。由于没有独立的物权行为概念,债权意思主义和债权形式主义的变动模式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处分行为”的概念,具有处分功能的是债权合同。因此,在这两种变动模式下,无权处分行为实际是指对特定标的物没有处分权的当事人所订立的,以引起标的物的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债权合同。 [11] 有学者不同意将未采处分行为概念的国家法律中的债权合同包括在无权处分行为中,理由是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区分“理论通顺”,并以我国《合同法》第135条为例说明我国民法上的处分行为不是债权合同:该条规定了出卖人占有转移和所有权转移的两项义务,其中所有权转移是一项独立于占有转移的义务,买卖合同并不发生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效力,标的物所有权转移义务履行后才发生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果。故买卖合同仅发生负担效力而不发生处分效力,从而将买卖合同定位于负担行为,因此出卖他人之物就不应再列入无权处分之列。 [12]笔者认为,物权行为理论背景下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确实存在于物权行为之中,但如果认为该效果意思只能存在于物权行为之中则是物权行为理论思维惯性的结果,是概念法学思维模式的产物。以买卖关系为例,买方订立合同的目的就在于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因此要求卖方承担给付义务即转移占有的效果意思和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效果意思完全可以同时包含在买卖合同这一债权行为之中。确实,所有权转移是一项独立于占有转移的义务,标的物所有权转移义务履行后才发生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果,但这个履行行为不一定必须是物权行为,同样也可以是债权形式主义下的仅需践行法定方式即可发生变动效果的事实行为。董安生教授就此问题也指出,物权行为中所包含的意思表示在法律意义上是对债权行为意思表示的重复或履行,它不可能具备有悖于债权行为的独立内容。 [13]实质上,物权行为的意思表示中并没有表达出比债权形式主义下的债权合同更多的东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债权意思主义下仅因当事人的债权合意即可发生物权变动,物权形式主义下物权变动由物权行为实现,这两种变动模式中的处分行为均能直接、当然地导致物权变动效果的发生。而债权形式主义下,债权合同作为具有处分因素的行为需要与履行行为结合,即通过履行法定的形式(登记或交付)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履行行为在性质上是一个事实行为。这是债权形式主义下这种处分行为的形态与前两者之间的最大不同之处。
三、区分逻辑在无权处分领域之贯彻
无权处分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中,最重要的是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之间,基于债权合同而形成的请求对方承担特定给付义务的和实现物权变动义务的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中的债权合同就是前述处分行为,对它的效力评价是处理无权处分问题的关键。在我国过去一些司法解释中,曾错误地将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一般认定为无效。《合同法》颁布实施以来,其中的第51条引起了我国民法学界关于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激烈争论,该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围绕该条文,我国学者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评价形成了物权行为效力待定说 [14]、债权合同无效说 [15]、债权合同效力待定说 [16]、债权合同有条件有效说 [17]、债权合同一般有效说 [18]等五种观点。前文所述,基于我国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事实,笔者将无权处分行为界定为具有处分因素的债权合同,而物权行为效力待定说将无权处分行为界定为物权行为,与本文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由于讨论无法在相同的平台展开,因此笔者不再对其观点进行评析。笔者赞成将作为无权处分行为的债权合同一般认定为有效,其它观点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在此对其进行讨论,但在下文笔者的论证中都会有所涉及。 (一)从区分原则看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认定
讨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必须结合另一有争议的条文,即《合同法》第132条,该条第1款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而根据第52条第5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此时有个问题,《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的内容是否属于强制性规定,无权处分的债权合同是否会因为违反该条的规定而导致无效?比如有学者虽然不赞同第132条第1款的规定, [19]但在解释该条款的性质时就认为:“该规定采用‘应当’作为判断词,显然是强制性规定。” [20]林诚二教授对此类问题进行了归纳并指出:对“应”字之规定,在具体情形有五种不同的解释,其中“应……,不得……”这种规范类型为训示规定,若不具备并非无效,仅有提醒作用;而“应……,否则……无效”为效力规定,若未按规定为之,才无效。 [21]王轶教授也认为,作为能够影响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必然是法律上的裁判规范,能够成为法官据以对合同纠纷作出裁判的依据,它应当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作出安排。 [22]《合同法》表述强制性规范和倡导性规范的条文并不存在明显区别, [23]这一点在该条款上表现得很典型。该条款应属于倡导性规范而非合同法上的强制性规范,不能据此因处分权的缺乏而使债权合同无效。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不受处分权缺乏的影响也是国际合同立法的发展趋势。比如《欧洲合同法原则》4·102规定:“仅仅由于合同成立时所负债务的履行不能或由于一方当事人无权处分合同关涉的财产,合同并不无效。”国际私法统一协会制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3·3·(2)规定:“合同订立时一方当事人无权处置与该合同相关联之财产的事实本身,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其理由之一就是:签约人的确经常在合同订立后获得对财产的合法权利或处分权,如果签约人事后未获得这些权利,则可以适用有关不履行的规定,使其承担违约责任。 有学者另辟蹊径,把第51条所谓处分权解释为处分能力乃至履行能力,以表明种类物、未来物买卖、连环交易、二重买卖等情形不属于该条所说的无权处分,而是有权处分,这些合同的法律效力不因此而受影响,从而把无权处分行为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 [24]笔者认为,这实为一种功能性的解释方法,是在解释这些场合虽然合同成立时标的物尚未确定或出卖人对该标的物无处分权,却需要将该类合同界定为有效,囿于第51条规定而进行的一种人为的法律构造。将处分权解释为处分能力不符合一般的认识,对处分权与处分能力具体情况的分析判断也较为复杂,而且从效果上看并不比将无权处分合同效力一般认定为有效的观点更优。比如该学者认为:“在我国现行法上,买卖等合同肩负着完成标的物权利变动的重任,虽然当事人对其财产具有处分能力未必每次均能完成这一任务,但他对其财产无处分能力,必然达不到这一目的,除非权利人追认。” [25]可是,既然在债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下,设定债法上负担的效果意思和实现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均存在于合同当中,就不能片面强调和追求合同中实现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而忽略合同本身对当事人的约束效力。且不说离开了债权效果意思,物权效果意思将无以依附,而且,当权利人不予追认的情况下合同无效,此时只能要求无权处分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而不是违约责任,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明显不利。 合同的相对性原理要求,无权处分人与买受人之间的以转让无权处分物为标的的合同,其效力情况既不因权利人的追认或无权处分人事后获得处分权而变得有效,也不因其相反而变得无效。一句话,其效力状态不取决于合同关系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包括权利人)。 [26]结合该原理,依据物权变动的区分原则,应该区分作为物权变动原因的债权合同与履行该合同所发生的物权变动效果,也就是说合同的有效不以公示的完成为要件,不以行为人有处分权为前提,也不以权利人的追认为条件,而应该依据合同自身生效要件进行判断。当行为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具备法律所要求的形式的情况下,即使最终不能基于该合同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也应该认定合同有效。处分权应是物权变动发生的要件,而非基础合同有效的要件。 (二)从区分原则看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的关系
在无权处分行为效力判断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关系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的重心,不在“取得”,而在“善意”,当与无权处分人进行交易的第三人善意时,其交易行为有效,至于其是否“取得”所有权,则取决于该有效之交易行为是否履行。善意取得主要不是物权法上的制度,而应为合同法中的制度。 [27]这种观点是违反区分原则的。就我国《物权法》第106条所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而言,其本身属于无权处分法律效果的例外规定,无权处分的债权合同虽然生效,但由于无权处分人处分权的缺乏,通常情况下不能发生所有权移转或他物权设定的效力,而只有在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时才例外地发生此种法律效果。善意取得在法律效果上的重心无疑是在权利的取得之上,善意取得制度规定在《物权法》第九章“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中也支持了这一点。善意取得从法律效果来看就是物权的变动,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判断与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发生是两个问题,因此不能将善意取得的发生与否作为判断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依据, [28]同样也不能将善意取得制度适用条件之一的善意要素反射到原因行为阶段,作为判断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债权合同有条件有效说的代表学者将未被追认或订立合同后未取得处分权的无权处分行为的生效条件进一步限定到,(除民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外)只要相对人在订约时是善意的并且支付了合理的代价,就可认定因无权处分而订立的合同是有效的。 [29]但即使是这样,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不满足这两项条件的法律行为是效力待定的。债权合同有条件有效说在利益安排的意义上虽然是对债权合同效力待定说的修正,但在这一部分的解释上与后者并没有差别,两者都背离了物权变动的区分原则。第三人的善意在判断其能否取得物权的时候才有意义,即善意第三人在让与或设定物权的行为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的情况下能够取得相应的物权,而恶意的第三人则不可以。 (三)从区分原则看《合同法》第51条
区分原则作为物权变动领域的重要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审视该领域其它规则的合理性。《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违反了由《物权法》第15条确立的区分原则(也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因此一般情况下应该排除该条的适用,并在将来立法中予以取消或改造。从立法论角度来看,《合同法》第51条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目的性过强,忽略了制度的整体性构建。按照通说(债权行为效力待定说)对该条文的理解,该条规定的思路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痕迹,即通过权利人的追认或者使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后获得处分权,从而使合同有效。 [30]这种思路的目的在于通过处分人获得处分权使合同发生当事人期待的效果,应该说初衷是好的,但在追求这一目的的同时忽略了制度的整体性构建。将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认为是效力待定,并赋予权利人追认权和买受人在合同被追认前的撤销权,确实理顺了追求合同生效这方面的关系。但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须以生效的合同为前提, [31]权利人不予追认的情况下合同无效,善意第三人无法善意取得该项物权,而只能要求无权处分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此时如何有效保护第三人利益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完满的回答。 二是路径依赖。《合同法》第51条的制订参考了《德国民法典》第185条和“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18条的处理方式,但是这种立法例是以德国和台湾地区物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下独立形态的无权处分行为为依托的。在把处分行为界定为物权行为的情况下,债权合同确定生效,物权行为效力待定,并不会阻碍第三人基于债权合同的请求权的行使。而中国大陆的立法并不承认独立的物权行为的存在,因此造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要在立法上避免这种逻辑矛盾,就应该在进行法律继受的时候对有关立法例进行仔细分析和甄别,并结合本国既有制度和实践需求进行选择。从区分原则对无权处分的影响,可看出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决定了不同的无权处分制度的法律构造,而不同物权变动模式具体又是通过区分原则来对无权处分的制度构建发挥着作用。
补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于2009年4月24日发布,该解释第15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实际上就极大地限制了《合同法》第51条在多重买卖情形下的适用,以弥补该条在法律效果上的不足。
|
| 注释: [1] [日]近江幸治:《民法讲义Ⅱ 物权法》,王茵译,渠涛审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2] 见《物权法》第6条。此外,该法第二章名为 “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所规定的实际上就是有关物权变动的内容。 [3]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4] 孙宪忠教授主张我国民法应当采纳物权行为理论,也主张用物权行为来理解我国的《物权法》。比如,《物权法》第127条第1款和第158条分别确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地役权自合同生效时设立的规则,一般认为此处的合同是债权合同,但孙宪忠教授认为:“对于这两种导致物权变动生效的合同,如果依据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来看,当然不可以将其理解为债权合同。原因很简单,依据债权合同只能产生债权意义上的请求权,而不能产生物权;所以这里的合同只能理解为物权合同。如果不承认物权契约,就不能理解这里的立法规则,而且还容易产生债权契约产生物权的误解。”参见孙宪忠:《我国物权法中物权变动规则的法理评述》,《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 [5] 孙宪忠:《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的区分原则》,《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 [6] 孙宪忠:《再谈物权行为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7] 孙宪忠:《我国物权法中物权变动规则的法理评述》,《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 [8] 参见田士永:《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312页。 [9] 张景良:《物权变动区分原则下类型化问题的解决》,《法律适用》2008年第1、2期。 [10] 参见黄松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11] 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12] 参见田士永:《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211-212页。 [13] 参见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121页。 [14] 参见韩世远:《无权处分与合同效力》,《人民法院报》1999年11月23日;丁文联:《无权处分与合同效力》,《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秋季号;张谷:《略论合同行为的效力》,《中外法学》2000年第2期;王闯:《试论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人民司法》2000年第11期;田士永:《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32页。 [15] 该种观点为王轶教授所归纳,并指出是少数说,但并未注明代表性文献。参见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203页。 [16] 参见梁慧星:《如何理解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8日;崔建远:《无权处分辨》,《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 [17] 参见王利明:《论无权处分》,《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孙鹏:《论无权处分行为》,《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 [18] 参见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13-216页;葛云松:《论无权处分》,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1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85页以下;董学立:《也论无权处分》,《法学论坛》2002年第3期。 [19] 参见田士永:《出卖人处分权问题研究》,《政法论坛》2003年第6期。 [20] 田士永:《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页。 [21] 参见林诚二:《民法总则》,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01页。 [22] 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07页。 [23] 参见王轶:《民法典的规范配置——以对我国〈合同法〉规范配置的反思为中心》,《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3期。 [24] 参见崔建远:《无权处分辨》,《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 [25] 崔建远:《无权处分辨》,《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 [26] 董学立:《也论无权处分》,《法学论坛》2002年第3期。 [27] 参见孙鹏:《论无权处分行为》,《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 [28] 比如有学者在讨论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关系时就认为,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符合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条件时,即使权利人拒绝追认,该因无权处分而订立的合同也是有效的。参见王利明:《论无权处分》,《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 [29] 参见王利明:《论无权处分》,《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 [30]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合同法》的释义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思路的痕迹,他们将“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而签订的合同必须经过权利人的事后追认或者在合同订立后取得对财产的处分权”作为无权处分他人财产而签订的合同的一般特点,并认为:“在权利人追认前,因无权处分而订立的合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在得到追认以前,买受人可以撤销该合同;在追认以后,则合同将从订立合同时起就产生法律效力,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请求对方履行合同义务。根据本条的规定,如果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该合同仍为有效合同。无权处分的本质是处分人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处分他人财产,从而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如果处分人在合同订立后取得了财产权利或者取得了对财产的处分权,就可以消除无权处分的状态,从而使合同产生效力。”参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载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flsyywd/minshang/2000-11/25/content_8365.htm,2006-12-18。 [31] 参见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2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