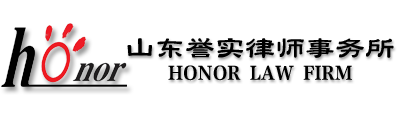一切都是熟悉的一切又都是初次相逢;一切都理解过了,一切又都在重新理解中 ——朱苏力
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秩序建构的困境,费孝通先生曾经感叹道: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制秩序的弊端却已发生了。在如何认识这种社会控制类型转变的机理上,理论界有不同的解读。本文旨在用一个视角重新探讨这一问题,并提出一些个人看法,力图为现代化规制形态的建构提供一种不规范但可能的道路。
一、古代中国的规制机理
中国哲学及文化对社会体系结构有着鲜明而富于特色的认知,集中表现在“家—国”关系上,集中体现了鲜明的伦理色彩。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人就是家庭关系的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家国相维,以家组国,齐家治国,家庭婚姻关系是中国社会组织的基础,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易经》有言:有天敌后有万物,有万物后有男女,有男女后有夫妇,有夫妇后有父子,有父子后又君臣,有君臣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我们将家庭婚姻关系是为伦理基础,并以此推衍初道德秩序,最后形成以宗法结构为基础的国家规制体系。这一体系充分借助熟人社会组织结构,努力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层面使伦理秩序外化为一套精神,并且形成能有效执行的社会制度,法制史上称之为“伦理法”。这种包含了为我们所熟知的“三纲五常”等伦理纲常的伦理法有效的回答了所谓的“安提戈涅问题”(即社区如何实现规范化自治),并维持了中国三千余年的社会秩序,创造了世界史上最为持久辉煌的文明。19世纪40年代以后,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冲击下,这种礼法秩序最终走向解体,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从此开始了对新的社会规制秩序的充满了血与泪的探索历程。
二、伦理法VS自然法
法理学告诉我们西方法治精神最早可以溯源于自然法观念,西方法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做一部自然法的发展史,起到了类似中国伦理法的功能。从比较法的视角上看,他们都为各自的社会治理秩序提供了正当性依据和方向性指导。不过,显然从运作机理上看两者差别巨大。
第一,批判法学家昂格尔将自然法观念视为西方法治产生条件之一,认为自然法将世界二元化为理念和现实,由于显示须符合理念之一规律的影响,自然法成为评价社会制度的标尺,因此自然法蕴含了潜在的“革命”因素,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便是一例。中国的伦理法,渊源于真实可感的血缘伦理关系,由于这种关系产生于人的本能(如父爱母爱),因而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在此基础上的中国社会秩序蕴含了保守性与稳定性,任何旨在“革命”的意识都很容易被视为“大逆不道”。
第二,在自然法观念中,人被视为平等独立的个体,基于天赋人权的认识,西方法中个人本位、独立自主观念浓重,并由此产生了以“自由平等互利”为核心的契约精神。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西方人视家庭婚姻关系是一种契约(康德曾对此论证),就算是国家也被认为是一种契约的集合(以洛克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标志)。社会契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使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成为必然,而契约精神本身所要求的“自由平等互利”观念则成为法治的灵魂。相反,在伦理法观念中,人一出生便被视为家庭社会关系的集合,拥有或即将拥有许多身份,一系列血缘关系身份的情调,是个人抽象为社会身份存在,家庭(团体)本位观念应运而生,个人意志的诉求成为异端,与家长制同时,专制制度形成,政治威权主义,国家父爱主义成为典型代表。由此东西方走向了不同的规制道路。
三、根源探寻
我们会也因该追问为什么东西方治理秩序会有天壤之别?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以自然法为代表的法治思想?答案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唯一的,但从历史哲学上看,单纯的意识分析是站不住脚的,更经不住考验。在此,我用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尝试做些简单的分析。
纵观中国古代史,土地问题,尤其是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流变过程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因之一。显然,历史上治世与乱世的出现,安定与变革,无一不与土地有关。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了中国的土地制度,结论是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根本制度,并作为经济基础影响了封建历史的发展。且不说中国是否存在所谓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但可以明确,它在古代中国并不是完整的,甚至不是“标准”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熟读历史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小农经济下的土地制度形态与教科书并不一致,而马克思也曾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而不是“封建生产方式”来分析中国社会历史,尽管学界尚未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但我认为中国古代分期,土地制度等核心概念有必要从中国的自身实际来定义,认识到理论的“地方性’”,不能用西方现成的理论来副会解释中国的现实,最终会曲解现实。)
我认为从井田制开始,一直到建国后的土地改革之前,两千多年的时间中国并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制度,是“不分公私”的(一人为私,两人为公)的存在。在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制度下,个人根本没有人格权,更不存在以人个独立为基础的法律意义上的物权即个人并不具有对物(主要是土地)的排他性支配权,个人与“物”分离的仅仅与“身份”结合。作为一种团体存在,在类似于“大同社会”的集体土地所有(不排除局部私有)下,个人对土地没有完整的物权,就不会产生所有权与用益物权的区分,也不会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二元化,既然经济领域不存在交换价值,交换关系就被遏制,商品经济也就无从谈起,更不会产生契约观念了,不仅造成了中国古代私法的不发达,更严重影响了古代“市民社会”的发育,因此现代法治理念缺乏了必要的土壤。总之,以土地所有制为核心的物权制度没有建立现代意义上的私有产权制度,产权混同且不明晰,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扼杀了契约精神,形成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结构的根源。
四、转型的困惑
世界大潮,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21世纪,自由民主人权为主流的现代西方治理理念成为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从传统治理模式向现代治理模式的转型成为我们迫切的任务。以市场经济发展培育公民社会,最终建立宪政体系的道路俨然成为学界主流。在这种呼声下,同时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法律理论的支持下,我们看到:股份制改革,物权法出台,中央全会解决土地流转权的决议等相关政策相继实施。不可否认他的成果,但在实施中我们看到了困惑:物权法依然无法解决个人与集体国家的产权矛盾,由此带来两极分化。法律规定流转权十几年后,农民依然无法掌握土地应有的利益。中国的秩序建构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转型的“阵痛”似乎越来越明显。
中国的社会规治结构需要转型,这是我们的共识,但所谓“法治”“宪政”民主“等一系列泛道德化的宏大话语在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的同时,也不免在实践中遭遇尴尬,法制从理论到实践走入困境,西方启蒙思想家描绘的理性社会渐行渐远见无穷”“日暮先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俨然成为现代法律人无声的“呐喊”。
五、总结并反思
我们总相信历史是多情的——尽管历史完全无所谓有情还是无情——我们需要而且会反思,烦死西方的经济和法律理论到死对我们的现实有多大的解释力,难道外国人比我们自己,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更了解我们自己?
与现实相比,任何学术理论都会黯然失色,都不过是一种解说,而且永远你不会有最后的解说。建国以来的公私之争的事实告诉我们:照搬的马克思理论行不通,西方自由主义那套也不行,我们只有走自己的道路,创造中国的产权理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的法治。我们要牢记苏力教授的那句话: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了他的法制,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治的理论。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创造了一切理论,我们这一代学子的工作就是深入到他的伟大实践当中去,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归纳理论用理论去知道伟大的实践。
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应有的贡献。这种贡献,只能产生于一种对中国昔日和现实的真切的和真实的关怀和信任,相信并假定:过去的和今天的任何人都打只和我一样具有理性他们的选择同样具有语境化得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深入的理解和发现现实,加以学术理论的概括和总结。缺少了对中国现实的关切仅仅停留在对旧有观念和西方现成理论的阐释上,不仅不利于学术自身的发展,更会危及到社会实践的推进,甚至是民族的复兴。“什么是我们的贡献”使我们是你是我,必须回答必须答好有能力有机遇答好的问题。我们责任重大,所以我们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但同时,作为一种反悖论,我们又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见证过历史,而今我们又在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