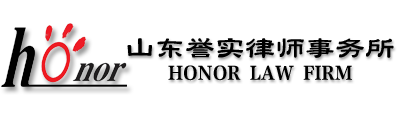【学科分类】刑法
【摘要】 南京大屠杀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暴行中最突出的一个事件,它的残酷程度令全世界感到震惊。但时至今日,日本国内仍有人要否认这段历史,认为南京大屠杀纯属“虚构”,要求中国撤走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的相关照片等。二战后东京国际法庭的审判是对日本战犯罪行的彻底清算。东京国际法庭的审判与二战中的反侵略战争一样,是对邪恶势力的清算。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比战争更具有长久意义的清算,因为它动用的不是军队,而是法律;它通过公开的审判,将日本军事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记录在案,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昭示后代,永志不忘。
【关键词】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录;惩治犯罪
【摘要】 南京大屠杀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暴行中最突出的一个事件,它的残酷程度令全世界感到震惊。但时至今日,日本国内仍有人要否认这段历史,认为南京大屠杀纯属“虚构”,要求中国撤走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的相关照片等。二战后东京国际法庭的审判是对日本战犯罪行的彻底清算。东京国际法庭的审判与二战中的反侵略战争一样,是对邪恶势力的清算。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比战争更具有长久意义的清算,因为它动用的不是军队,而是法律;它通过公开的审判,将日本军事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记录在案,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昭示后代,永志不忘。
【关键词】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录;惩治犯罪
【正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地投降至今已有62年,为了清算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侵略罪行而成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又称为“东京法庭”)审判结束至今也有59年的历史。然而,日本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本国曾有过的侵华历史,至今还坚持着予以否定的立场和态度。他们不管是在慰安妇问题、细菌战问题、劳工问题还是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全然不顾其他国家的感情、不顾历史事实和国际社会舆论,采取极力否定的态度。
2007年6月19日,由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中约100名国会议员组成的“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议员会”发表“调查报告”,妄图否认南京大屠杀,声称当年中国遇难者大概仅为“两万人”,“没有超过普通战事中的死亡数字”,等等{1}。另外,日本议员中有的甚至认为南京大屠杀纯属“虚构”,要求中国撤走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的相关照片等{2}。“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议员会”还汇总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三点结论,宣称:“一是当时在南京派驻特派员的日本媒体均没有有关大屠杀的报道纪录。二是南京陷落后的1938年,中国国民党政府向国际联盟提交文件,称‘南京两万人被屠杀,数千人被施以暴行’,呼吁国际联盟谴责日本的行为,但当时的国际联盟并没有通过对日本的制裁决议。三是攻陷南京的日本‘仝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在东京审判中被定为无罪。”{2}
这完全是在颠倒是非,一派胡言。
对南京大屠杀,近60年前的东京国际法庭早有定论。日本国会议员认为南京大屠杀中国遇难者仅为“两万人”、大屠杀纯属“虚构”的论调真是胡言乱语,胆大妄为地否定远东国际刑事法庭的判决。虽然对“调查报告”的程序以及这些谬论是如何得出来的过程不太清楚,但笔者对国际刑法有专门研究,并于1995-2002年在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工作,先后担任法庭法官的助理法律顾问、检察长办公室法律顾问及上诉检察官。从国际审判(尤其是东京审判)的程序和机制方面来看,法庭判决都是基于严格被审理并被接受的证据之上,被告在审理中具有平等诉讼和反驳的权利;程序和证据规定方面都有严格限制,如“无罪推定”原则;对受害人的受害程度的认定,也都有确凿可靠的证人证言作为基础,如“排除任何怀疑”原则等。即便东京国际法庭有时很慎重、甚至在拿不准的情况下会显得比较保守,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残酷暴行却是被法庭认定的事实,没有任何疑问。
是可忍,孰不可忍。针对日本国内的这股极右势力,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近60年前的东京审判的记录,驳斥这些极端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重正历史。
一、东京国际法庭与历史记录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轴心国的失败而告终的。德国的正式投降是在1945年5月8日,日本的正式投降是在1945年9月2日。在德、日投降之后,战胜的同盟国便分别在德国纽伦堡和日本东京先后设立了两个国际军事法庭,以便把轴心国的某些国家领导人当作首要战争罪犯而加以逮捕、侦查、起诉、审读和判刑。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1条规定:“依照……协定,应设立一国际军事法庭,以公正并迅速审判及处罚轴心国之主要战争罪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1条也规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设立,其目的为公正与迅速审判并惩罚远东之主要战争罪犯。”所以,这两个国际军事法庭的成立,就是要审判当年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政府中对策划、准备、发动或执行侵略战争有最高或主要责任的人。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一开始时规定,法庭成员由5名以上、9名以下法官所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的人选系由盟军最高统帅从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9个受降国所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任命。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后,盟军最高统帅对它进行了修改,将法庭成员国又增加了两个。这样,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6年5月3日正式开庭时就有11名法官。他们分别来自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印度和菲律宾。另外,这些国家还派有检察官来负责法庭的起诉和检察工作。中国政府派遣的法官和检察官分别为梅汝璈和向哲浚。
在纽伦堡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受审的人,都是对德国和日本侵略战争政策的制定和侵略战争的进行起过重大作用的。对他们通过正式组织的国际军事法庭依照法律手续加以审讯和制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国际法历史上的一个创举。在这以前数千年的历史上,一个战败国的领导人物,即使他们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巨魁,一般都是逍遥法外的,从来没有受过法庭的审判和法律的制裁。一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显要在战争中一旦落在敌国手中被杀害或被囚禁的事情,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成立两个国际军事法庭,用法律去制裁战败的领导人之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新创举。
纽伦堡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理,就是为了将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政府和军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记录在案。有一个典型的案例能清楚地展示国际军事法庭的这一目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战胜方的同盟国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随即,美国第8军登陆日本对其实施军事占领。在“密苏里号”战舰签字仪式结束后的第9天,驻日盟军总部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署了盟军总部第一号逮捕令,下令立刻逮捕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39名甲级战犯。命令下达后,30多名美国宪兵包围了东条英机的住所,但就在这时,屋里传出一声沉闷的枪声,原来东条英机在里面想要自杀,但自杀未遂。当美国宪兵冲进去时,他摇摇晃晃地站在那里,手上拿着一支0.32英寸口径的科尔特手枪,鲜血已经染红了衬衣。此时,美国宪兵二话不说,马上就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并为此主动献血给他。
东条英机生于1884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毕业,毕业后长期任职于陆军省、参谋本部及关东军司令部。1940年10月晋升为陆军大将,1941年10月18日至1944年7月22日任日本首相。他是日本法西斯集团中最激进的一个,也是其领导人之一。1940年,他推动日本加入轴心国集团并在此后控制了整个日本的军队,是参与对华侵略、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主谋。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5条明确规定:“本法庭有权审判及惩罚被控以个人身份或团体成员身份犯有各种罪行包括破坏和平之远东战争罪犯。”所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管辖的国际罪行主要有三个,即:战争罪、反人道罪和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就是指“违反战争法规及战争惯例之犯罪行为”,其范围非常广泛,如杀人放火、奸淫、虐待俘虏、残害平民等各种残暴行为;反人道罪则是纽伦堡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提出的新罪名,其依据源自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纳粹德国希特勒暴行的清算和预防;破坏和平罪其实就是今天经常提到的“侵略罪”,它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是列为第1项的犯罪,次序排在战争罪和反人道罪之前。
东条英机被指控犯有反和平罪与战争罪,并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经过二年半的审理后,于1948年11月12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侵略罪和战争罪被判处绞刑{3}。
东条英机最后被判处绞刑。然而自杀未遂、生命处于危险状态时,美军宪兵不仅立即把他送到医院抢救,而且为了让他活下来,还主动献血救他。美国军人的目的就是因为他作恶多端,不能让他用自杀来逃避公理与正义的审判。在还没有开庭之前,东条英机必须活着,必须接受公开审判,以便让世人了解真相并彻底粉碎日本军国主义体制。
南京大屠杀无疑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暴行中最突出的一件,它的残酷程度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或许仅次于纳粹德军在奥斯威辛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正如下面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法庭判决书所认定的,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比起德军在奥斯威辛单纯用毒气的屠杀,其杀人方法是残酷绝伦、多种多样,无奇不有。宋希濂认为南京大屠杀“实为现代战史上破天荒之残暴记录”。它的残暴程度比起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有过之而无不及{4}(P. 30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对日本战犯的罪行的彻底清算,也是国际社会中的正义力量与邪恶势力的较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继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为中心的轴心国以军事上的失败而告终,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犯下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是对中国乃至对整个人类犯下的罪行。这些日本侵略者与希特勒法西斯集团一样,是人类中最为邪恶的势力。因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与二战中的反侵略战争一样,是对邪恶势力的清算。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比战争更具有长久意义的清算,因为国际军事法庭动用的不是军队,而是法律;它要通过公开的审判,让世人以日军暴行的真相来警示一代又一代的后人。所以,当东条英机自杀未遂后立即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并为了让他活下来接受审判还主动献血给他,其意义正是为了能够记录日军残酷的暴行,为了世界永久的和平。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争罪犯的审判之所以能够进行,背景是因为美、苏、中等国对日本侵略者的反侵略战争取得了胜利,但最终能够将那些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绳之以法,则是通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而取得的历史性的重要成就。尤其是对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松井石根这三名双手站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的审判,如果没有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这些人的滔天罪行就不可能被记录在案,也不可能得到应有的惩罚。通过审判将日本军事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记录在案,是为了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为了昭示后代,永志不忘。
二、平等诉讼原则与保障被告权利
东京国际法庭的判决,对将日本军事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记录在案意义重大。这不仅因为法庭本身是依法成立,而且在实体法和程序上都是严格按照规则来实施,体现了法律的公正和历史的公正。
1. 程序规则的基本原则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所有活动都以该法庭的《宪章》为基础。它由东京盟军最高统帅列克阿瑟于1946年1月19日以特别通告的方式颁布的。《宪章》共分5章,17个条款。主要内容涉及该军事法庭的组织、人事、行政、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在法律问题中,实体法方面规定法庭的审判权力,也就是对人和对罪行的管辖权、刑罚权和程序方面的规定等。程序方面的规定包括陈述的顺序、审判的进行,证据的被接受、对证人如何诘问、判决的型格、刑罚的执行等。所有这些内容,在宪章里都有清楚的规定。
定罪证据必须经法庭审查,作为证据的物证也必须在庭上出示。法庭在规则和实践中强调,一切定罪证据均应经过法庭出示、审查。只有被法庭认可、采纳的证据才能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依据。在程序上,东京审判对每个证据的认定都经过主讯(examination-in-chief)、反诘(cross-examination)和再主讯(re-examination)。
实质意义的控、辩平等,就是指调查和起诉阶段中的平等。其具体要求是:
(1)检察机关行使追诉权也要尊重法律上保障人权的规定,并负有维护嫌疑人、被告人权益和保障司法公正的义务;
(2)嫌疑人或被告人享有以辩护权为核心的一系列诉讼权利,尤其包括判决前随时得到律师帮助的权利,在诉讼中享有与检察官平等的提证权、问证权。
(3)法官在庭审中对控、辩双方的意见和证据材料应予平等的重视,对各方的利益予以同等尊重和关注。
除了控、辨双方平等以外,作为国家或国际社会刑事追诉者的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还负有一项特殊的义务,即它要始终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并要达到最高的证明标准。换句话说,控诉方承担证明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从法律上讲,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的直接依据在于他必须推翻无罪推定的假定,被告人是没有为自己申辩无罪的责任。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控诉方提出指控的目的在于推翻嫌疑人、被告人被推定无罪的原始地位,因而必须承担证明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另一方面任何人都不大容易或不大可能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无罪,更何况处于受追诉地位的嫌疑人、被告人。
所以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告人,在诉讼中无需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对自己诉讼主张的证明,只需达到较低的证明标准;对于可能使自己陷人刑事控罪之中的事项,被告人拥有拒绝陈述的权利等等。这样,作为强者的检察官与作为弱者的被告人,经过法律程序的矫正,就大体上在对抗手段、对抗能力和对抗机会方面拥有平等的地位。
证明责任是指控诉方承担的证明嫌疑人、被告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全部事实或基本事实的责任,具体内容包括:
(1)控诉方应向法庭出示据以指控的所有证据材料,如书证、物证、鉴定结论、视听资料等并证明证据的合法性。
(2)控诉方应向法庭陈述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并运用足够的证据进行充分论证,达到足以推翻被告人无罪的推定。
(3)对被告人提出的辩护理由,控诉方“有责任来驳斥它,而不是被告方有责任来证明它。”
关于指控犯罪成立的证明责任是不能转移的。所以在整个审理过程中,由检察起诉方承担证明被告有罪的责任和义务。
2. 控辩双方诉讼平等原则
东京审判遵循的诉讼平等原则。也就是说,控辩双方当事人在东京审判中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不存在一方地位高于他方的情形。从诉讼结构的角度来看,普通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与审判官的距离相等,呈等腰三角形的外观。其中审判官处于等腰三角形的顶点,居中立的裁决地位,控辩双方由分别排在等腰三角形底边与两腰的交点之上,呈对抗的姿态。在法官眼中,即便是代表社会利益的公诉人(检察官),也和被告人一样,是当事人之一,两者地位平等。双方的差异只是在于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主张不一致。所以在前南国际刑庭的组成结构上,检察长办公室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但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它又是一个当事者,作为控方而享有与辩方同等的诉讼权利。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这种审判方式被称之为对抗式审判。在现代国际社会中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刑事审判类型,即对抗式审判(adversarial)和讯问式审判(inquisitorial)。前者适用于英美法系国家,后者则主要为大陆法系国家所实行。前南刑庭的审判方式,基本上是普通法系国家的对抗式的方式,但同时又融合了大陆法系讯问式的色彩。
对抗式审判(又称辩论式审判)主要是基于相对哲学和公平竞争的理念。依据这一哲理,刑事案件的事实真相,应当由那些与案件结局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诉讼双方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通过对抗而得以揭示,法庭审判也应当以诉讼双方的对抗性活动为主线而进行。公平竞争则意味着起诉方和被告方应当站在相同的基点上,平等地展开诉讼攻击与诉讼防御活动。
与平等诉讼原则相联系的还有“无罪推定”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任何人在被确定为有罪前,都应视为无罪的人来对待,所以被告在整个审理过程中享有与之相适应与起诉检察机构相同的诉讼权利。检察起诉方与被告方具有平等对抗的机会和权力。
无罪推定原则假定被告在最后被定有罪之前是无罪,因而是一种带有明显保护性的法律假定原则。无罪推定事实上为控辩双方的对抗提供了一种抑强护弱的制度保障。刑事诉讼一启动便出现控诉方和嫌疑人、被告人直接对立的局面。相比较而言,拥有强大国际社会支持的检察起诉方显得实力强大;追诉权面前的嫌疑人、被告人则处于弱势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保证控辩双方在程序上的平等,就会导致辩护职能的弱化,从而使诉讼职能出现失衡而不利于司法诉讼的公正解决。从这意义上讲,控辩职能的平等是推动诉讼程序公正运作的保障。
根据控、辩双方之间平等的原则,控辩方在法庭审理阶段都有权传唤证人提出证据。顺序是控方提出证据,辩方提出证据,控方反驳证据,辩方再反驳证据。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法庭自己也可以提出补充证据,或传唤证人。
3.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人证言
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常突出的事件,所以东京审判非常重视。1946年9月,为了弄清“南京大屠杀”事件真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来进行法庭调查和审判。据梅汝璈法官的回忆,法庭用了差不多3个星期专门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此事件的中外证人(人数在10名以上)的口头证言及检察和被告律师双方的对质辩难,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讯,真实地记录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这些暴行是“现代战史上破天荒之残暴记录”。
与东京法庭的法官相对应,在盟军最高统帅部之下设立了国际检察处。作为一个起诉机关,它由11国各派1名检察官组成,在审判中作为原告代表11个国家。由于起诉机关负责对甲级战犯控诉,权限非常大,所以,首席检察官由美国人季楠担任。由于检察起诉工作的独立性,法官与检察官各自独立,彼此地位平等但又不同。东京审判的国际检察处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其他国家的检察官只是处于顾问或助手的地位。
与东京审判中的法官或检察处人员比较精干相比,法庭审理中的辩护机构十分庞大,人员众多,这也是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的一个重要区别。东京审判中的每个被告不仅拥有2至6名不等的日本律师,而且还有美国律师(共20多名)的帮助,整个辩护队伍达到了310人{4}(P. 273)。
在东京审判中,检察官逐个传讯检察方的证人,逐一出示实物证据,以证明被告确为罪犯。在东京审判就南京屠杀第一个作证的,是当时在南京大学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罗伯特. 威尔逊。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医术高超,心地善良。在许多中外同事逃离南京避难的时候,威尔逊留了下来。他目击了日本人在南京的血腥屠杀。就在他的医院里,不断有被日本兵刺伤、砍伤、烧伤和强奸或者死里逃生的人被送来,这个拥有180张床位的医院始终爆满,从1937年12月13日开始,在六、七个星期里日本军队一直在屠杀中国人{5}(P. 64)。
为了证实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曾经邀请过3个死里逃生的中国证人出现在法庭上,他们是南京居民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5}(P. 64-65)。
尚德义是个难民,1937年12月6日和哥哥尚德仁、堂兄尚德全一起被抓,被带到长江边上的下关,与其他1000人被机关枪扫射,死里逃生。
伍长德于1937年12月15日被侵华日军从南京难民区抓走,和其余的2000多名难民一同被带到汉西门外。日本军人用四挺重机枪向手无寸铁的难民扫射,伍长德在枪响之前倒地,幸免一死,但接着又被侵华日军的刽子手刺刀乱捅,煤油焚烧,伍长德疼得滚入护城河,侥幸逃脱。伍长德是在大屠杀中身上被日军浇上了煤油而未被焚烧致死的唯一的一个幸存者,他那使人惊心动魄的证言给审判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还有一个叫陈福宝的难民,在侵华日军进城的第二天从避难地区被抓走。当时,在南京,日本士兵只要看到戴帽子、手上有茧子的人就会立刻枪毙,其中大部分是平民。两天以后,他再次被抓,日本兵让他们摔跤,输了的就会被刺刀捅死。
以上这些幸存者在法庭上的证词惊心动魄,给所有在场的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尚德义与伍长德、陈福宝的证言在经过被告方的质询之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接受,认为他们的悲惨经历反映了当时日本军队野蛮的行径。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期间,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向东京法庭提供了包括中国和美国人在内的13人宣誓作证词。曾经到南京等地实地调查的美军上校托马斯·莫罗检察官向法庭提供了约翰·马基神父拍摄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共8件证据确凿的宣誓证词。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得到的一份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在法庭上,这段影像资料被检察方面作为物证当庭放映。
这是由一部16毫米老式电影摄影机拍摄下来的历史胶片,画面记录的是侵华日军进入南京进行大屠杀的影像资料。拍摄这些画面的人,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基。他于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陷南京时,担任国际红十字南京委员会主席,亲眼目睹了侵华日军烧杀淫掠的血腥场面,冒着生命危险用摄影机拍摄了长达105分钟的真实史料。
约翰·马基在东京审判作证时说“他们(日军)采用各种各样的途径进行屠杀,通常由个别日本兵进行,但很快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屠杀,有数百人是刺刀捅死的,有个妇女诉说日本兵将她的丈夫捆缚后,就在她的眼前扔到水池里而被淹死的,她什么也做不了,他就在她的眼前被淹死。”约翰·马基神父的作证和他出示的胶片资料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所有人感到惊愕不已{5}(P. 66-67)。
东京法庭在审理“南京大屠杀”事迹时,还接受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作证文件,那就是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拍发给德国外交部的一封秘密电报。由于这封电报是德国投降后盟军搜查德国外交部机密档案库时发现的,而且它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是与日本结盟国家所提供的,所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所有法官都非常重视这份电报。该电报在概括地描述了侵华日军在南京杀人如麻以及强奸、放火、抢劫的普遍情况说:“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3}(P. 485)正是这部“野兽机器”将中国南京变成了人间地狱。
三、被告的反驳权利与检察官的举证责任
以上东京国际法庭对日军在南京的残酷暴行的认定,不仅是因为证据本身确凿可靠,而且它还是在被告行使了他们的反驳权利后被认定的。
在东京法庭的庭审中,被告有反驳的权利。每当检察方传询完所有的证人,并在直询中出示了所有的证据以后,就转到被告一方传询自己的证人,出示自己的证据,这一刑诉程序称为“被告的反驳”。被告的反驳程序与检察方的传证一样,也是一个一个的传证人,一件一件地出示证据。
1. 被告质询的权利
在东京国际审判中,当事者还有质询的权利。所谓质询(cross-examination),就是在某一证人作证完毕以后,由对立一方的律师问话。需要首先强调的一点是,之所以会有质询是因为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程序与普通法系国家的一样,检察官和被告双方在案子的审理中各有各的证人,分得清清楚楚。检察方和被告双方的证人,是双方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和案情分析确定的。不言而喻,检察方的证人所作的证词,都是要证明被告有罪的;被告方的证人所作的证词,自然都是要证明被告是无罪的。在东京审判中作这样一条规定,其根本目的是保证审判的公平。它认为通过质询,证人的有意编造和无意的误述都可以有效的暴露,从而有利于弄清事实的真相。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讯程序对被告辩护方面作了保障性的规定。为了使审讯公平合理,被告的辩护权利得到尊重。该法庭《宪章》规定每一被告有权自行选任其辩护人。事实上,它虽规定每一被告“有权自行选任其辩护人”,但却没有关于每一被告在拥有多少个辩护人方面的限制性规定。结果在实践中,东京国际法庭的每一被告都拥有美国辩护律师至少一名,而日本律师的名额则更漫无限制,有的被告如岛田繁太郎的辩护律师竟达8名之多,一般被告每人也有5名或5名以上{4}(P. 273)。
前南京政府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出庭作证时,他在直讯阶段的书面证言宣读不过一、二小时,而在反诘阶段中辩护律师们向他提问题竟花了4天多。又如,伪满皇帝溥仪出庭作证的时间总共是8天,但直讯阶段的时间是半天,而被告律师们轮流反诘的时间则占了7天半{4}(P. 254)。
所以,从东京审判的实践来看,被告的辩护权得到充分的保障。东京国际法庭对被告“过分宽大”,它对被告传唤的证人名单没有进行过严格认真的审查。从法庭程序上来看,邀请什么人出庭作证主要是由诉讼双方自行决定的事。但是按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9条(戊)项的规定,在核准证人名单时,法庭应该命令当事人除指明证人所在地址外同时说明需要他出庭证明之事实以及经等事实与本案审讯的关系。法庭如果在这些方面有所不满,就有权拒绝传唤某些证人。但事实上,东京国际法庭并没有这样做。它对诉讼当事人申请传唤证人一事几乎是采取“有求必应”、“来者不拒”的态度,很少进行过严格认真的审查。因此,在审讯过程中,证人川流不息出庭作证。检察方面所提供的所谓“检察证人”有109名,而被告方面所提供的“辩护证人”竟有310名。从数量上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接受出庭的“辩护证人”的数目几乎等于“检察证人”的3倍。
从东京国际法庭的诉讼程序上看,虽然起诉方和被告方都有“质询”的权利,但因为举证上的规定,对检察方的要求就更严格。
在东京法庭的案子审理中,举证责任完全由公诉人(检察方)承担。由于法庭适用的是普通法系的规则,所以被告被定有罪的标准规定得非常高,即检察、起诉的证明必须达到“排除任何合理怀疑”(be yond any reasonable doubt)的程度。
具体解释就是: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由于被告被证明有罪之前是被假定无罪的。所以检察官必须出示足够的证据以证明被告有罪。在国际刑事法庭,证明的标准很高,如前所述,要达到“超越了任何合理怀疑”的程度。证据是否足够,就看这些证据(包括证人的证词和实物证据)所证明的程度是否已经“超越了任何合理怀疑”。所谓超越任何合理怀疑,就是说,如果一个正常而不带偏见的人在听完了检察官方面的所有证人的作证,看完了检察官方面出示的所有实物证据后,如果对被告是否就是罪犯这点上不存在任何的“合理怀疑”,那么被告就可被判有罪。
“超越了任何合理怀疑”的概念,来源于普通法系国家的司法制度。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证明标准。在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中,证明一般分三个层次。最低程度的证明叫做“合理性证明”(reasonable basis)。意思是说,当一个正常的人把所有的证据不带偏见地审查一遍,如果他认为从向法庭展示的证据来看,被告“很可能”(a significant possibility)犯有其被指控的违法行为,那么这个证明就是成功的。也就是说,只要证据的天平往一边倾斜,重的一边就算是完成了证明。这种证明大多用于民事案件。
中间程度的证明叫做“明确、可信证明”(probable cause)。这一级的要求比合理性证明要高。但到底要高出多少,才算是明确、可信,这也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但不管怎么样,它也算是给了裁判者一个比较大的尺度。一般在欺诈等民事案件证明中,要求必须达到这一证明程度。
最高程度的证明就是“超越合理怀疑”。超越合理怀疑是从反面看问题,着眼点不是证明者证明了多少,而是他还有多少没有证明,而如果这些没有证明的地方构成了合理怀疑(reasonable doubt),那么证明就算失败。
2. 东京法庭的定罪标准
在东京审判中,东京法庭定罪的证明应当达到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1)据以定案的证据具有关联性,即对案件真实具有证明作用,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如被告人的前科、相似事件、品格等,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2)据以定案的证据必须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并且其真实性、可靠性得到控辩双方交叉提问、质证的证实;
(3)对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提出证据的一方需提供进一步证实其真实、可靠性的补充证据,特别是对非原件的文书证据和传闻证据;
(4)据以定案的证据必须是合法取得的,并且以法定的证据形式表现的,如果对证据的合法性存在争议,提出的一方对证据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5)根据控辩双方已提出的证据,可以肯定犯罪是本案被告人所为,排除任何其他的可能性,也就是对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排除了合理的怀疑;
(6)当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控方,即公诉人和自诉人)不承担举证责任、无法举证或举证达不到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时,法院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超越合理怀疑本是普通法系国家国内刑法上的证明标准,本来就很高。但由于国际刑事法庭要严格适用国际标准,所以在国际刑事法庭对检察官提出的证明标准实际上是更为严格。在每一个案审中,检察官方面必须确实要证明到“超越合理怀疑”的程度,才能定被告人有罪。而在被告方面,根据“一切被告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为无罪”的原则,则不需要证明任何东西。在理论上被告方面可以坐在法庭上什么也不做,让检察官方面传讯完了证人以后,直接等待法官决定检察官是否已证明到“超越合理怀疑”的程度。由于对检察官有这么一个要求,所以当被告律师传讯证人时,他并不是要努力证明什么,而主要是是想通过证人和证词,在检察方陈述的案情中找出一些漏洞,目的是在法官的脑子里留下一些“合理的怀疑”。如果被告律师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指望国际刑事法庭判定被告无罪。
东京审判中的证明标准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也就是说,检察机关要证明被告有罪,其提出的证据必须能够排除一个正常人对这些证据可能产生的任何怀疑。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从事实和法律两个不同的角度,对检察官的指控进行有力的反驳,并提出和论证对被告人有利的辩护证据。检察方则必须在法庭上以法律为根据、毫无保留地出示其所掌握的全部证据。如果不这样,其所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就有不被审判法庭认可的可能。换句话讲,起诉方如果不能出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以证明被告所被指控的罪行已经清楚地具备了(不是“可能具备”也不是“不太确切地具备”)其所有的构成要件。否则,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就不能认可公诉人指控的相应的犯罪事实。
所以,反诘在凭证程序中是特别重要的。梅汝璈法官在谈到关于南京大屠杀审判情况时认为:“一个证人的证言如果不经过反诘的考验,它的证据价值是非常微弱的。假使一个证人在直讯中是信口雌黄、胡说乱道,在反诘阶段必定会被对方驳得体无完肤,弄得焦头烂额。反之,如果证人在直讯中说的都是亲历目睹、有凭有据的真实情况,那么,在反诘中他便会理直气壮、满怀信心,对对方的诘问必能从容对付,对答如流,不予对方以任何可乘之隙。正如俗话所说,‘真金不怕火炼’。在审讯南京大屠杀事件时出席法庭作证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几乎全是这一类的证人。他们的证言真实,态度坚定,在反诘中那些被告的日本和美国辩护律师虽然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想出许许多多千奇百怪的问题向证人提出,但都经他们一一予以有力的回击,弄得那些律师们自感无趣,啼笑皆非,结果只有偃旗息鼓,知难而退。”{4}(P. 258)
所以,即便规定了如此严格的证明标准,东京国际法庭通过确凿可靠、不容置疑的证据,认定日军在南京城所实施的暴行。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上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早晨,当日军进入市内时,完全没有遭遇到抵抗”。“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南京市像被捕获的饵食似的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该市不像是由有组织的战斗部队所占领的;战胜的日军捕捉他们的饵食,犯下了不胜计数的暴行”。“日军单独地或二三成群地在全市游荡,任意实行杀人、强奸、抢劫和放火,当时任何纪律也没有。许多日军喝得酩酊大醉,在街上漫步,对一点也未开罪他们的中国男女和小孩毫无理由地和不分皂白地予以屠杀,终至在大街小巷都遍地横陈被杀害者的尸体”。“中国人像兔子似的被猎取着,只要看见哪个人一动就被枪杀”。“由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在日方占领南京的最初两三天的工夫,至少有一万二千的非战斗员的中国男女和儿童被杀害了。”{3}(P. 484)
日军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我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我同胞,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以及他们认为是可能参加过抗日活动和适合兵役年龄的我青壮年同胞,进行过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而这些屠杀又是以最残酷、最卑鄙的方法实施的。例如,在12月15日(即占领的第3天),我已放下武器的军警人员3千余名,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均饮弹殒命,其负伤未死者亦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又如,在同月16日(即占领第4天),于华侨招待所的男女难民5千多人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用机枪射杀后,弃尸江中,使随波逐流,企图灭迹{4}(P. 300)。
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上说:“强奸事件很多。不管是被害人或者是为了保护她的亲属,只要稍微有一点抗拒,经常便遭到杀害……在这类强奸中,还有许多变态的和淫虐狂的事例。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还将她们的躯体加以斩断。”{3}(P. 484)
东京国际法庭还接受了无数的关于这类强奸及奸后杀戮的证据,并对此作了认定。例如,幼女丁小姑娘,经日军13名轮奸后,因不胜狂虐,厉声呼救,当即被割去小腹致死。市民姚加隆携眷避难于斩龙桥,其妻被日军奸杀后,8岁幼儿及3岁幼女因在旁哀泣,均被用枪尖挑其肛门,投入火中,活活烧死。年近古稀的老妇谢善真在东岳庙中被日军奸后用刀刺杀,并以竹竿插穿其阴户,以资取乐。民妇陶汤氏在遭日军轮奸后,又被剖腹断肢,逐块投入火中焚烧。这类不胜枚举的残酷无比的奸杀暴行,在南京被占领后差不多两个月的时光内(迟至1938年2月初旬,情况才开始好转),每天几乎都要发生几百件,乃至于上千件。因此,远东国际法庭的认定是:“在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左右的强奸事件”;“全城内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奸污了”{4}(P. 309)。
东京法庭判决中具体提到了幼女丁小姑娘、姚加隆妻女、年近古稀的老妇谢善真、民妇陶汤氏等,这些认定都是根据法庭认为确凿可靠的证言而写入判决书中的。仅仅从以上这些人的遭遇就可以看出日军是怎样穷凶极恶以及我数十万呻吟于敌寇铁蹄下的南京无辜同胞的命运是何等悲惨!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这些事实的认定都是根据可靠的证言写入判决书中的。以上日军暴行的中国受害者有名有姓,完全确凿可靠。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梅汝璈法官认为,“东京法庭的这个认定和数字估计完全是根据曾经向法庭提出过的那些确凿证据而慎重地作出的,绝对没有夸大。其实,当时的实际情况还要比这坏得多。”{4}(P. 310)
四、法庭对受害者的认定与对罪犯的惩治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全部审讯过程中接受采纳的诉讼双方所提供的作证文件共为4336件,其中检察方面提供的是2734件,辩护方面提供的是1602件{4}(P. 262)。
所有检察方面传唤出庭的证人不但都曾亲自出庭并作口头的或书面陈述,而且根据规则都得经过对方的反诘,有的还经过了再直讯和再反诘的考验。最后,他们的证言被法庭采纳为证据,就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们的证言可信,没有任何问题。
东京审判坚持关于刑法的基本原则。例如,东京审判中有一个“不能自证其罪”的原则(rul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这是英美法系里一条由来已久的传统原则。依照这个原则,被告有权在法庭上拒绝作任何可以使他自己陷于有罪嫌疑(即所谓“自入于罪”)的供认或发言。因此,在审讯中,他完全可以拒绝回答检方向他提出的任何问题。这是英美法系向来用以保障人权的非常重要的一项规则。美国并把这项规则列入宪法修正案中,认为它是公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之一。
按照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规定,被告如聘有律师代为辩护,自己便可以不出庭辩护。这项规定,表面看来好像是限制被告的辩护权,实际上是给被告以逃避亲自直接受审的机会。狡黠的被告们便选择不出庭作证,例如土肥原贤二,他在整个审判期间就讲过一句“无罪”,其他时间都保持沉默,这样就使得法庭和检察官同他们没有任何直接的接触或交锋。就是对于那些自愿登台作证的被告们,法庭的讯问和检察官的反诘也只能限于他们在直讯中提供的主要问题,而不能对他们的全部罪行做彻底的、有系统的追究或盘问。
任何刑事被告有权拒绝答复任何可以使他自己陷于犯罪地位的问题。因此,这也就给了他在审讯中完全拒绝发言的权利。这项规则的用意原在保护被告,使他在受审时不致因为自己的无知、胆怯或疏忽,或者由于法庭和检方的威胁压迫,而作出不利于自己的招认。刑事被告既有权完全拒绝发言,那种“严刑逼供”和“屈打成招”等违反人权的现象从理论上讲当然就不会发生。
然而,“不能自证其罪”的原则,适用于普通的简单的国内刑事案件还有道理,但把它适用到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审理的这样复杂的国际案件,就有点不合适。因为在这样复杂的国际案件中,有些情况如果不是通过直接审问被告就不可能会弄清楚。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刑事法庭严密的程序和证据规则,也不可能会发生对被告们威胁的情况。所以,“不能自证其罪”的原则,与国际刑法上的另一原则,即“迅速而公平”地进行审判的原则又是相矛盾的。这也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为什么会持久两年半的原因。它从另一方面,也说明被告的权利在东京审判中是得到充分尊重的。在这种情况下的判决书,反映了历史事实,因而也体现了公正。
1. 东京法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认定
经过长达两年半的审理,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在其判决书上裁决道:
“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十五万五千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根据这些团体的报告说,尸体大多是被反绑着两手的。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毁了的尸体,以及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3}(P. 486)。
对于东京法庭的这个判决,需要细读,其中有几点尤其需要注意:
第一,远东国际法庭这个估计无疑的是慎重和保守的。它认定南京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为在审理中能够确切地被证明的被害人至少已经有20万人;法庭在这里提到的“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精确地说,就是由红十字会掩埋的43071人以及由崇善堂收埋的112261人,这些数字是由这两个团体的负责人各自根据该团体当时的记录和档案向远东法庭郑重提出的,是经过被告在行使了反驳和反诘权后被法庭认定的。
第二,远东国际法庭在认定南京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的同时,还郑重声明:“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毁了的尸体,以及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法庭的这一声明,是因为在审理中注意到日军灭迹伎俩的狡黠和多样化。它们在将人残酷地杀害后往往还灭迹。例如,在汉中门外被枪毙的被俘军警3千余人的尸体均被焚化;在中山码头被射杀的难民5千余人的尸体均被投入江中;在下关草鞋峡被密集扫射杀死的平民57400余人的尸体亦均被焚化,等等{4}(P. 314)。考虑到这些暴行可能已无迹可寻,或有些被发现稍迟来不及向法庭提出证据,故法庭作了一个保守的认定,即受害人“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
第三,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被远东国际法庭认定被杀者为“二十万人以上”的数字,不仅未包括尸体被日军消灭了的大量被害者在内,而且这个数字仅仅是“在日军占领后六个星期内”的被杀者的数字。从南京大屠杀的背景情况来看,日军占领后的六个星期是日军的杀人高潮,但是在这六个星期以后,他们的杀人勾当并没有完全停止,只是大规模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减少了,而个别的、零星的或小规模的屠杀却仍在经常地进行着,这一类的被屠杀者的数字并没有被包括在远东法庭所认定的那个数字之内。
如果把以上所举的种种因素考虑在内,我国参加东京审判的梅汝璈法官认为:“估计在日军占领时期,我南京无辜同胞被杀害的人数必定是在30万至40万之间。这个估计绝非主观臆测,而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它同远东国际法庭的估计是丝毫没有矛盾或抵触之处的。”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不但杀害我数十万同胞,其所用的手段也极其的残忍。例如,日军在南京最大规模的集体屠杀是在下关草鞋峡进行的那一次。那次屠杀是在12月18日(即占领的第六天)夜间举行的。当时日军将我从南京城内逃出而被拘囚于幕府山的男女老幼共57418人,除少数已被日军饿死或打死者外,全部都以铅丝捆扎,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使饮弹毙命;其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均遭乱刀砍戳;事后并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目的也是为了灭迹{4}(P. 306)。
日军对于这些集体屠杀,认为死者的尸体被投诸江中或焚为乌有,就自以为无罪迹可寻,但是在大量的证据面前,这些暴行已经是铁案如山、不容抵赖的了——在汉中门外、中山码头和下关草鞋峡,我国共有65000多无辜同胞被日军杀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还发现了好几处“万人坑”、“千人冢”,其中在灵谷寺旁的一处且有敌伪时期南京督办高逆冠吾为三千余无主孤魂所立的一块碑文。这些坑冢无疑的是日寇搞集体屠杀的罪证,是他们使用活埋这一种屠杀方法的有力证据。通过法医对挖掘的数千具尸骸检验的鉴定报告推定:集体活埋确是日军使用的集体屠杀方法之一。
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除了任意屠杀我国同胞之外,便是随时随地强奸我国妇女。其次数之多,情状之惨,被称为世界之最。因此,在世界舆论中,“南京屠杀事件”有时还被称为“南京强奸事件”。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认定的事实来看,日军在南京实施的强奸和杀人经常是连在一起的。日本军队在强奸之后通常是把被奸的妇女、甚至连同她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
据此,梅汝璈法官认为,奥斯威辛的大屠杀和南京的大屠杀在性质上和方法上都是不尽相同的。首先,奥斯威辛的屠杀是根据纳粹的种族仇视政策和希特勒政府的直接命令有计划、有系统的屠杀,并且是用一种方法(毒气)进行的;而南京大屠杀则系在长官的放任纵容下由日本兽军不分青红皂白、随心所欲地胡干乱干的。其次,在奥斯威辛那个遗臭万年的“杀人工厂”里,它是把所有的屠杀对象分批地、集体地送入毒气室用烈性毒气在几分或几秒钟内杀死的;而南京大屠杀则除了集体屠杀之外,大都是由日本兽军个别地或成群地随时实行的,在屠杀之前大都先加以侮辱、虐待、抢劫、殴打、玩弄或奸淫。德军的屠杀大都是单纯的屠杀,而日军的屠杀则是同强奸、抢劫、放火及其他暴行互相结合的,其屠杀的方法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狂虐残暴的程度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4}(P. 302)。
2. 东京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罪魁的惩治
东京国际审判记录了我数十万人民于日寇铁蹄下的悲惨命运,用事实展示了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写真图”。尽管如此,东京国际审判还是运用国际法律的规则来对实施南京大屠杀的罪犯追究其个人刑事责任。
松井石根是一个应对南京大屠杀负有主要责任的人。攻陷南京城并进行残酷屠城的共有4个师团,即谷寿夫第六师团、中岛第十六师团、牛岛等十八师团、末松第一一四师团。而统率所有这四个师团则是松井石根大将。他当时是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官,也是攻打南京的最高统帅,因此他对南京大屠杀无疑的负有最高的责任。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松井石根被列名于日本“甲级战犯”之中,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的28名日本首要战犯之一。在东京审判中,松井石根就是根据“指挥官责任”原则而被定罪的。
在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理论和实践中,“指挥官责任”已成为一个常用术语,也是追究高级军事指挥官和社会高层官员个人刑事责任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从法律方面来看,指挥官的刑事责任一般是指这两种情况:(1)指挥官命令下属或其他人员实施犯罪;(2)指挥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下属将要实施犯罪而没有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来阻止犯罪,或是在行为发生后知道但没有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来惩罚罪犯。
根据“指挥官责任”(command responsibility)原则,军事指挥官如果“知道或者由于当时的情况理应知道”其部队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犯罪行为,以及该军事指挥官没有采取在其权力范围内的“必要而合理的措施”以防止或制止这些犯罪行为的实施,那他(她)也应对这些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
根据国际法中关于指挥官责任的理论,一个上级(指挥官)在其部下实施了战争罪、反人道罪或种族灭绝罪等国际犯罪行为时、如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正在或将要实施的这些犯罪行为而没有采取合理、必要措施来阻止或惩罚该犯罪者,则不能免除该上级(指挥官)的刑事责任。
国际法中之所以有指挥官责任这样的理论,是因为在像军队这样等级严格的组织中,指挥官因为其地位而具有法律上的责任。如果军队行为没有受到指挥官的命令限制,就一定会有违法犯罪行为。国际人道法的目的是保护平民和战俘不受残酷地对待,要实现这个目的就需要指挥官尽责。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审讯中,松井石根试图为他所犯下的罪行进行开脱。在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和美国检察官莫罗出庭指控以松井石根为首的侵华日军使中国南京居民深陷极大的痛苦和暴力之中,妇女遭到野兽班的奸淫,一群群侵华日军暴徒用枪弹、刺刀不停地制造举世罕见的死亡和恐怖等事件之后,松井石根出庭为自己辩护。
松井石根为自己辩解说:“虽然我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但我的部队攻占南京时,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大概还是有一些情绪失控的士兵和军官干出胡作非为的事情来的。这是十分遗憾的,我是后来才听到这种过失的。”莫罗质问道:“你作为进攻南京的最高指挥官,怎么能说后来才听说发生这种‘过失’呢?”
松井石根说:“攻打南京的当时,我正在距该城140公里的苏州卧床养病,并不知道他们违抗我的命令,竟干出这班暴行来。12月17日我到达南京后,从宪兵司令部那里第一次听到这种意外事件并严惩肇事者,因此,把全部罪责都加在日本军官和士兵头上是不公平的,我是在日本投降后才第一次听到南京惨案的。”
松井石根强调他在大屠杀时并不知情。然而,据在法庭作证的国际安全区西方人士说,他们除了对日军进行规劝以外,曾通过新闻记者向世界舆论通报日军的暴行,并将这种种暴行作成“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向日军当局每天提出两次抗议。然而,日军当局从未理睬,亦不置复,依然任其部下肆虐如故。
针对这一情况检察官曾讯问松井石根是否看到过这些“备忘录”?松井石根答称:“看到过”。检察官又接着问他是否采取过什么行动?松井答称:“我出过一张整肃军纪的布告。贴在某寺庙门口。”检察官问道:“你认为在浩大的南京城内,到处杀人如麻,每天成千成万的中国男女被屠杀、被强奸,这样一张布告会有什么效力吗?”松井哑然,无言以对。
松井石根继而又供称:“我还派了宪兵维持秩序。”检察官问共多少名宪兵?松井答:“记不清,大约几十名。”检察官问:“你认为在好几万日军到处疯狂地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情况下,这样少数的宪兵能起制止作用吗?”松井于沉思后低声答称:“我想能够。”于是,检察官方面遂传讯证人。证人根据他所目睹的事实,在法庭上证明当时南京全城总共才有日本宪兵17名,就是这17名宪兵,非但不制止任何侵华日军暴行,而且自己也加入了暴行的行列,特别是抢劫财物或者从强盗士兵手中做第二次抢劫。在证人证言面前,松井石根无地自容{5}(P. 72-74)。
所以,作为最高的军事指挥官松井石根,在日本军队占领南京后纵容他们实行野蛮的屠杀。他辩护时提到了生病,然而,他的疾病并没有阻碍他指挥作战行动。他的军队犯下了极其野蛮的战争罪行,这些部队属于他指挥。他知道这类暴行,但没有去预防,更没有惩治,如果不是他故意纵容部下,南京大屠杀事件便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其规模亦必然会小得多。因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后裁决:松井石根是南京大屠杀案的主犯和祸首,并判处他绞刑{3}(P. 612)。
五、对南京大屠杀的抵赖与东京审判的意义
日本国会议员在2007年6月通过所谓“调查报告”来否认南京大屠杀,声称当年中国遇难者大概仅为“两万人”,“没有超过普通战事中的死亡数字”,有的甚至认为南京大屠杀纯属“虚构”,并要求中国撤走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的相关照片等,是对东京审判的否定,是对历史的否定。然而,日本的这种否定由来已久。日本国会议员在2007年6月的这一次,既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就在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发生不久,日本就开始了其否定这段历史的活动。于1948年12月公布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就揭露道:“1938年2月5日,新任南京守备队司令官的天谷少将,在南京日本大使馆中曾对外国的外交团发表声明,对于将南京日军暴行的报告及送各国的外国人态度加以指责,并非难这些外国人是煽动中国人的反日感情。”{3}(P. 488)
这是1938年。相隔近70年的时间里,日本国内就一直有人继续不断地在否定这一历史。然而,历史就是历史。东京审判已经真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
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对我南京同胞的屠杀极端残酷野蛮,其方法又是多种多样。除了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任意枪杀之外,日军对我无辜同胞还用尽了其他种种的杀人方法,例如: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割生殖器、砍去四肢、刺穿阴户或肛门等;举凡一个杀人狂患者所能想象得出的最残酷的杀人方法,他们几乎都施用了,而且在南京沦陷后持续6个星期之久的时间里,每天都要对我无辜同胞施用成千上万次,这确实是骇人听闻、史乏前例的残暴记录。
但这中间最残暴、最令人发指的还是日军为取乐而举行的“杀人比赛”。
1937年11月30日到12月11日期间,侵华日军第16师团步兵19旅团第9联队第3大队少尉向井敏明、野田毅两人在南京被日军占领之后,在全城杀人如麻的空气中,忽然别出心裁地决定要进行一次“杀人比赛”的游戏,看谁用最短的时间能杀死最多的中国人。杀的方法是用刀劈,就像劈柴或我国南方儿童玩的“劈甘蔗”游戏一样。同意了比赛条件之后,这两个野兽便各自提着极其锋利的钢刀,从上海杀向南京的途中展开了杀人竞赛。他们分头走向大街小巷,遇到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便是当头一刀,砍成两半。
对于向井敏明、野田毅两人的这种兽行,当时的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的《每日新闻》却把它当成是日军的“英勇行为”连续做了突出报道,而且是图文并茂。在他们每个砍杀的人数都达到了一百的时候,他们便相约登上紫金山的高峰,面朝东方,举行了对日本天皇的“遥拜礼”和“报告式”,并为他们的“宝刀”庆功、祝捷。在这以后,其中一名又添杀了5个中国人,另一名却添杀了6个。于是,后者便以接连杀了106个中国人而被宣布为这场“杀人比赛游戏”的“胜利者”。
1947年底,南京法庭在向井敏明、野田毅这两名战犯衩引渡到中国之后对他们进行了审判,并以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将他们两判处死刑。
事情发生在60年以前,但还远没有结束。
自日本首相小泉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有所抬头,在国内大肆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特别是借编撰历史教科书等机会大翻历史旧账,图谋为二战中的侵略者翻案。在这一背景之下,日本右翼势力却挑唆向井敏明、野田毅两战犯的家属出来翻案。
2003年4月28日,沉默了多年的“百人斩”杀人竞赛凶手家属向井千惠子(现名田所千惠子)等3人,向东京地方法院控告日本原《朝日新闻》记者、朝日新闻社、每日新闻社。控诉书长达18页,称上述被告的报道和书籍“侵犯了当事人及其家属遗属的名誉”。因此,要求上述被告刊登谢罪广告,停止书籍的继续出版,并赔偿精神损失费。
2003年8月23日,日本东京地方号法庭以“本多氏的著述也不能完全说是虚构的”,“无法认定报道内容系捏造”为由,驳回了田所千惠子等人的控告。可是,这些人对一审判决不服,遂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日本高等法院于2006年5月24日判决原告败诉,认为无法证明“百人斩”是捏造的{6}。
东京高等法院对“百人斩”报道诉讼案作出判决,维持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驳回日军战犯家属的上诉。日本高等法院判决之后,日本各界反响强烈。不仅“当事者”《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立即进行了报道,《读卖新闻》、《产经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东京新闻》等也都发表了评论,普遍认为这一历史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东京审判对我国意义重大。在我国现代历史上,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及中国人民受到西方列强无数次的侵略,在1945年前没有一次取得胜利。中国的财富被掠夺、被压榨到没有一滴油水的地步,中国人民为此也受尽了种种屈辱和痛苦。抗日战争是中国反抗外国侵略中第一次真正的胜利,东京审判则是使中国人民真正得以扬眉吐气的一个大事件。
回顾东京审判,让人真切地感觉到:历史事实尤在,社会良知尤在,正义尚存。东京审判过去已有59年的历史了。我们绝不能因为审判的结束而忘却这桩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浩劫。相反,我们以及子孙后代都应该牢记日本侵略军的这桩滔天罪行,并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正如我国梅汝璈大法官所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4}(P. 306)
尾声
前不久听到一个消息,说在中国与日本学者之间将就历史问题举行对话。尽管我不太清楚这一对话要达成的结果,也不知道其程序是如何制订,但可以肯定一点:如果对话的历史其中包括1928年到1945年这一段,就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东京关于日本侵略中国历史的审判,就是从1928年起算的。通过审判,这段历史不但已经清清楚楚,而且是在具有司法保障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一个国际性的司法机构审理并作出的定论。学者讨论不可能比这个更清楚,也不可能会比这更有权威。学者讨论结果中任何与东京审判判决不相符合的地方,都可能会造成对历史的伤害,这意味着会给中国人民造成第二次伤害。
东京审判真实地记录了历史。对这段历史,我们永志勿忘。
【作者简介】
朱文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人道法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欧洲法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兼职教授。
【注释】
《文史资料选辑》(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第22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转载于梅汝璈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律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第300页。
【参考文献】
{1}王燕. 日百名议员,安图否认南京大屠杀[N]. 法制晚报,2007-06-20(A27).
{2}林雪原,林梦叶,汪析. 日议员妄称南京大屠杀“虚构”[N]. 环球时报,2007-06-21(2).
{3}张效林,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M]. 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4}梅汝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
{5}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编. 丧钟为谁而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纪实[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
{6}右翼怂恿家属出面,主流社会已感厌烦[N]. 环球时报,2006-05-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