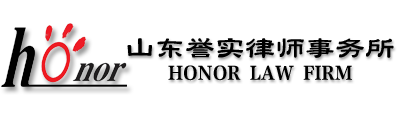【摘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应当限定在以侵犯相关人基本权利的手段获取的证据,“毒树之果”不应属于排除范围。非法证据的排除只应限定在该证据在证明被告人有罪方面不具有可采性,其效力并不及于其他方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有赖于“二元式”裁判结构的建立;有赖于科学的动议、听证和裁判程序的建立;有赖于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
【正文】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的一大缺憾,莫过于曾经进行过论证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终未被立法者所采纳。虽然后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确立了有限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由于其制度设计不甚合理,加之配套机制的缺失,收效甚微。非法取证这一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的顽症,没有在根本上得到解决。就目前的形势和现实状况看,尚有必要进行相关的深入讨论,以使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制度安排
(一)哪些非法证据应当排除
证据自身本无合法与非法之分。“非法”一词无疑是针对取证手段而言的,在英文中“非法证据”一般表述为evidence illegally obtained,也正是从取证手段的非法性上来界定的。因此,讨论非法证据范围,必须从分析非法取证的性质和程度入手。
司法实践中的非法取证行为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手段收集证据;另一种是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收集证据,但并未对公民的基本权利构成侵犯。前者主要表现为侵犯相关人的身体健康权、意志自由权、隐私权、住宅不受侵犯权、财产所有权等,这些权利是法治社会中人之所以为人之最基本权利,也是各国宪法保护的重点;后者则表现为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未遵守某些程序规定,例如,勘验现场时未邀请见证人到场等。笔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应限定在第一种类型中,第二种类型收集的证据不应当属于排除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将第一种类型获得的证据称为非法证据,而将第二种类型获得的证据称为“有瑕疵的证据”。
虽然各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规则不尽相同,但设立这一规则的目的或初衷是相同的??都是从人权保障价值出发的。换言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证获取证据的真实性,也主要不是为了规范取证行为,而是为了维护证据收集过程中对相关人基本权利的尊重。证据排除规则在建立和适用过程中,实际上面临着一种权衡和选择:一方面是证据的证明价值;另一方面是取证手段的违法程度。只有当某一证据的取证手段侵犯了相关人的基本权利时,排除这一证据的使用才能实现人权保障的初衷;而如果某种证据的取证手段没有侵犯相关人的基本权利却排除该证据的使用,既不能实现犯罪控制的目的,也对保障人权没有意义,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即使在美国这样程序高度发达的国家,在有关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也是以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作为排除标准的,而对于那些不违反公民宪法性权利的一般违法取证手段则称为无害错误,所获取的证据当然不会在排除之列。
由是以观,应当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据包括如下三种类型:
1. 以下列方法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 (1)刑讯; (2)威胁、欺骗; (3)使人疲劳、饥渴; (4)服用药物、催眠。
2. 以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的方法,而进行的搜查、扣押行为所获取的实物证据。
3. 未经合法授权而进行的监听、采样、电讯截留等行为所获取的证据。
上述三种情况无疑都会严重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中,第一种类型有的侵害了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如刑讯、使人疲劳、饥渴;有的则侵害了公民的意志自由权,如威胁、欺骗、服用药物、催眠。第二种类型侵害了公民的住宅权和财产所有权;第三种类型侵害了公民的隐私权;不论是侵害身体健康权还是意志自由权,结果都违背了供述的自愿性原则。这些基本权利在我国宪法中都有明文规定,如果对这些权利进行侵犯,所进行的取证行为便失去了合宪性基础,所获取的证据当然应当排除。
笔者不同意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做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的区分。在笔者看来,非法证据是否排除不应根据证据的类别而有区别,而应视非法取证的性质和程度而定。实物证据如果是通过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手段获取的,同样应当排除;相反,言词证据的获取中如果没有侵犯相关人的基本权利,则不应当排除。例如,笔者就没有将《法院解释》第61条所规定的“引诱”列入其中,因为引诱在非法程度上不同于威胁和欺骗。威胁和欺骗侵犯了公民的意志自由权;而引诱则并不导致相关人意志自由权的丧失,对是否进行陈述仍然可以做自由选择。此外,在实践中也很难在正当的盘问技巧和引诱之间进行区分。
(二)“毒树之果”应否排除
“毒树之果”,是指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为线索,再用合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其中,前面用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是毒树,后面用合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是毒树之果。例如,犯罪嫌疑人在刑讯之下供述了赃物的隐藏地点,然后通过合法方法搜查提取了该赃物,或者在一项非法侵入犯罪嫌疑人住宅的搜查中获取了赃物,再以该赃物为线索找到了被害人,并用合法方法对被害人进行了询问。因此,应当明确的是,“毒树之果”中的“果”应当是独立的新证据,而不是原有证据的重复收集。先通过刑讯的方法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然后再用合法的讯问方法让犯罪嫌疑人将原口供重述一遍等做法,仍然属于非法证据范畴,而不是“毒树之果”。因为实质上,这种情况下该证据还是通过前面的非法行为获取的,而不是通过后面的合法方式获取的。
“毒树之果”应否排除,各国做法不尽相同。美国虽然通过判例确定了毒树之果的排除规则,但又通过一系列判例确定了例外;日本虽然也认为毒树之果不具有可采性,但附加了十分严格的条件;英国则不排除“毒树之果”的可采性,不管是普通法还是成文法都采取排除“毒树”,但食用“毒树之果”的原则,典型的例子就是排除被告人供述这一事实并不影响从该供述中发现的证据的可采性。排除“毒树之果”对于非法取证行为来说,无疑是最彻底的釜底抽薪的治疗方案,但问题是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如果对“毒树之果”也予以排除,有可能彻底堵住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大门。因此,各国对待这一问题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我国目前现实条件下,应当借鉴英国的做法,“毒树之果”不应当排除。首先,“毒树之果”中的“果”,是通过合法的方式取得的,本身并没有侵犯相关人的基本权利;其次,犯罪控制也是刑事诉讼中不可忽视的目的之一。非法取证行为只能导致这一行为所获取的证据无效,而如果将这一效果无限扩大到阻止一切证据信息暴露的程度,犯罪控制的目标将会受到过度伤害;再次,“毒树之果”的排除非常复杂,程序观念高度发达的美国,也不得不通过判例建立起一系列例外规则,这些例外规则基本上使排除“毒树之果”规则无用武之地;最后,我国是一个有着“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传统的国家,警察收集证据的能力和手段还不十分先进,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排除非法证据尚且需要进行艰苦的论证和说服工作,再提排除“毒树之果”很不现实,相反倒有可能欲速则不达,连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目标都难以实现。
(三)对非法证据应当排除到什么程度
对非法证据应排除到什么程度?是不是经过排除之后,该证据便永远从某一案件的证据库中消失了?这是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研讨中被忽视的一个问题。
强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人权保护方面的价值,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那就是私人收集或者提供的证据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只有当某一证据是享有国家公权力的警察或者其他调查官员非法收集时,才会导致对相关人基本权利的侵犯。私人即使采用一些违法手段收集了证据,如秘密录音,如果对案件有证明价值,也不应当排除。即使是警察或者其他调查官员非法收集的证据,适用排除规则也只应局限在不能适用该证据认定被告人有罪,并不意味着该证据的证明价值彻底丧失。至少下列几个方面非法证据的证明价值应当承认:一是非法证据不能用来证明被告人有罪,但可以用来证明被告人无罪。使用非法收集的无罪证据不但不会伤害到相关人的基本权利,反而具有促进人权保护的功能。正因为如此,显然不应当将刑讯之后被告人的无罪辩解排除在证据体系之外。二是非法证据不能用来证明被告人有罪,但可以成为量刑时考虑的因素。排除了某一非法证据的可采性之后,案内的其他证据仍然能够达到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标准的时候,在量刑阶段不应当再次排除该证据。几乎所有国家有关证据能力或者可采性的规则均是针对定罪而言的,其效力不应及于量刑阶段。三是非法收集的实物证据不能用来证明被告人有罪,但可以用来作为质疑被告人法庭审判中陈述可信性的手段。非法收集的实物证据虽然手段是违法的,但其真实性可以保证,这一点上与言词证据是有差别的。因此,当被告人在法庭上进行虚假陈述时,通过提出实物证据来质疑其陈述的真实性,便不应当被禁止,因为此时提出的实物证据已经转移了其证明目标??不是用来证明被告人有罪。四是非法证据不能用来证明被告人有罪,但可以用来作为指控收集证据的警察或者其他调查官员非法取证行为的证据。即可以通过揭示非法证据信息的不合逻辑或者违反经验规则,来证明非法取证行为存在的可能性。
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程序构建
(一)现行裁判结构能否满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需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是为了排除而排除,其根本目的在于隔断非法证据信息同事实裁判者之间的联系,使该证据对事实裁判者最终认定被告人有罪时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而要达此目的,在程序设置上一个必备条件便是必须存在两个彼此独立的裁判程序:一是实体性裁判;二是程序性裁判。实体性裁判的任务是运用具有可采性的证据对案件事实做出裁判;程序性裁判的任务则是将那些不具有可采性的证据排除于事实裁判者的视野之外。由此看来,不仅实体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在诉讼阶段上应当是分离的,在裁判主体上也应当是分立的。如果实体性裁判者同程序性裁判者合二为一,非法证据即使被排除了,该证据信息对案件事实认定的影响却是很难消除的。美国证据法学家达马斯卡将这种程序性裁判与实体性裁判分离的裁判结构称为“二元式结构”,他同时认为证据的“排除”,只有在这种“二元式”的裁判结构中才能真正实现。“二元式”裁判结构还可以有另一种解读,即定罪裁判和量刑裁判的分离。前者专门负责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后者则是对已经认定有罪的被告人确定刑罚。这样一种意义上的“二元式”裁判结构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也是极富价值的:一方面可以使非法证据在定罪裁判中毫无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使该证据信息在量刑阶段闪亮登场,成为量刑法官最终确定已被定罪被告人刑罚的重要因素。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程序中,显然不存在上述两种意义上的“二元式”裁判结构。既没有程序性裁判;定罪裁判和量刑裁判又是合二为一的。用“一元式”来形容我国的裁判结构是再恰当不过了。在这种“一元式”裁判结构中,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内的所有证据能力规则很难有效地运行。一方面,由于程序性裁判的缺失,大量缺乏证据能力的证据涌向审判法官,对审判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影响无法消除;另一方面,由于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合二为一,使得实践中在使用证据排除规则上畏首畏尾。正是这样的“一元式”裁判结构造就了即使是最高法院规定的有限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也鲜有适用的现象。笔者可以断言:我国现行的裁判结构不能满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需要,改革这种裁判结构势在必行。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引进“二元式”裁判结构,建立程序性裁判程序并实行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离。
程序性裁判应当置于实体性裁判之前,由不同于进行实体性裁判审判法官的预审法官进行。凡是有关包括非法取证在内的程序性争议,都可以经相关人申请启动程序性裁判程序。在程序性裁判中,应当有控辩双方参加且采取公开的听证方式。经过这一程序,预审法官应当就非法证据是否排除问题做出裁决。当事人对程序性裁判不服,应当允许独立上诉。增设程序性裁判,表面上增加了诉讼成本,但是其对诉讼公正和效率价值的实现却是无法估量的:第一,程序性裁判可以取代现行的庭前审查程序,使庭前审查程序承担起更多的功能;第二,程序性裁判可以使后来的实体性裁判程序中争执点更加集中和突出,审判更富效率;第三,程序性裁判给当事人铺设了一条获取司法救济的通道,诉讼更加公正;第四,程序性裁判可以完全阻断非法证据同实体性裁判法官之间的联系,审判更加中立。
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分离的基本方式是,将现行的审判程序改造成为定罪程序,即经过审判之后只做出被告人是否有罪的裁判。然后再在现行审判程序之后增设量刑程序,专门负责确定被认定为有罪的被告人的刑罚。量刑程序和定罪程序的法官可以同一,但在量刑程序中除了原有的控辩双方当事人以外,还应当邀请被告人所在单位、社区人员参加,他们可以就被告人的一贯表现、人身危险性等问题发表评估意见;在程序性裁判程序中被排除的非法证据也可以在量刑程序中提出,成为法官量刑时考虑的因素;还应当邀请被害人参加,他们可以就被告人的量刑提出要求。笔者认为,实行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离,既可以实现刑罚的个别化原则;又可以充分听取和尊重被害人的意见,加大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力度。既可以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犯罪控制方面的副作用降到最低程度;又可以解决现行审判中出现品格证据而导致的审判不公现象。
(二)非法证据是自动排除的吗?
当人们在讨论某一非法证据要否排除之时,该证据一定是已经过收集、提取和固定程序,在形式上已经具备成为证据的一切要件了。如果这一命题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要回答非法证据能否自动排除的问题自然涉及三个子问题:一是谁来提出排除的动议?二是谁来决定排除?三是该证据是自动排除还是裁量排除?
正如前文所述,非法证据之所以要排除,是因为该证据的取证手段侵犯了相关人的基本权利。认定某一取证行为是否侵犯相关人的基本权利,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某一取证手段虽然客观上有侵犯相关人基本权利的行为,但相关人本人并不认为侵犯了他的基本权利,或者说他自愿接受这种侵犯,便不能认为这一取证手段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意义上的非法取证行为。这一立论,是建立在个人意思自治以及私权可以处分和让渡的法理原则基础之上的。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都在坚持强制侦查行为程序法定原则的同时,又接受相关人同意前提下的非法定例外。从这一立论出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程序的启动,一定要以相关人或者经过其授权的人提出排除动议(或者称为申请)为前提条件。美国联邦法院在卡兰德拉案中,就坚持以“个人亲身权利”标准,将被非法取证手段侵犯的相关人或者经其授权的人提出排除动议,作为排除程序启动的条件。
某一非法证据是否排除,其决定者是法官(程序性裁判法官) ,而不是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规定检察机关要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排除某些证据的使用。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自觉对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拒绝使用侦查机关非法获取的证据,当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也是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则实在没有必要。国内有不少学者认为,在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上,存在自动排除和裁量排除两种模式,这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所有国家的非法证据都是通过裁量排除的。只要承认非法证据排除本身是一项程序性争议,承认该争议的解决客观上存在着动议的提出、证明、听证和裁判程序,就不会有自动排除的可能。即使是有些学者主张的自动排除的那一类情形,实际上也是裁量排除的,因为法官在排除该证据以前必须就该证据的取证手段是否确实达到了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程度进行裁量。因此,笔者主张未来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中只要明确规定哪些非法证据属于排除范围,并建立起科学的非法证据的动议提出、证明、听证和裁判程序即可,而没有必要再做自动排除和裁量排除的区分。
(三)如何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证明责任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证行为的彻底否定,而某一取证行为是否属于非法行为则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因此,研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证明责任,是构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根据惯例,诉讼中主张积极性(肯定)事实的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而将消极性(否定)事实引入诉讼的当事人无需对此承担证明责任。依此原则,在刑事诉讼中,检察官一般作为提出被告人有罪的积极追诉请求的一方,他同时也必须以充分的事实为根据来加以论证,那么对于证据本身合法性的证明,必然属于证明积极请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被告人提出的证据非法的异议,则属于消极(否定)性事实,当然无需承担最终的证明责任。
举证能力毫无疑问也是证明责任分担中的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技术性因素。诉讼中举证能力较强的一方应承担较多的证明责任,反之,证明责任就会较小,这既是追求纠纷解决的便利性、迅速性的必然要求,也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的体现。一般而言,国家为了追诉犯罪,赋予检警机关以巨大权力,诸如讯问、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等,在检控方利用这些手段进行刑事侦查过程中,被告人一般会处于检控方的控制状态之下,并且,被告人通常也缺乏必要的法律常识和技能,即使有辩护律师在场协助,他也无法将控方取证(特别是非法取证)的全过程记录下来。比较来讲,控方则有这种优势。这种力量悬殊的对比局面决定了审判中证明自身行为合法性的负担也就必然地主要落于控方头上。
从价值因素上讲,现代刑事诉讼中,由控方承担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证明国家行为的合法性,是追求国家理性、司法理性的必然要求。并且,对于国家在与公民直接对话与交涉的过程中实施的非法行为,一旦相对人诉求于司法,国家就必须对其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提供一定的事实、法律根据予以证明。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行为,刑事侦查过程中的取证行为给公民权利、自由带来的危险性比一般的行政行为更大,那么,对于此种程序行为正当性的证明责任由取证方来负担亦属理所当然。
在我国现行侦查体制之下,警方取证一般处于自我授权、缺乏监督的权力封闭状态,并且侦查活动中缺乏律师的参与,讯问中缺少全程录音、录像,搜查、扣押无法受到中立的司法审查机关的制约。凡此种种,促使我们有必要将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完全赋予控方。具体而言:第一,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当被告方基于一定的理由对控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时,控方必须承担其证据合法取得的证明责任;第二,被告方对证据合法性的异议所需的理由只要使取证行为的合法性“有合理的怀疑”即可,比如,被告方提出口供笔录中前后不一致等;而控方证明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则必须达到“排除合理的怀疑”;第三,当控方未能证明其证据为合法所得或证明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时,法院应当推定该证据系以非法手段所得,并依据法律的规定予以排除。
余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件“舶来品”,这项规则有其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由于篇幅和论题所限,本文只能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身的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进行研究。但如果要想使这一制度能够在未来中国刑事诉讼中被接纳并且有效运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首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排除而排除。理想的状态当然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用得越少越好,而不是越多越好。如果有一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仅是一条宣示性规则,实践中几乎没有非法证据需要排除,中国的刑事法治便达到了最高境界。但问题是,要实现上述目标,监督和规范取证行为的一系列制度便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制度如讯问嫌疑人时的律师在场制度,讯问时的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沉默权制度以及证据开示制度等。
其次,只要承认非法证据不是自动排除,而是法官(程序性法官)裁量排除的,那么法官在具体证据的排除中就具有重要作用。而法官究竟如何排除一项证据,除了制度层面的因素以外,还有很多政策性和技术性因素需要考虑。这些问题即使再高明的立法也是无法解决的;而如果让各地法院自行其是,又有损法制的统一性。因此,最高法院针对实践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建立起系统的、比较有影响力的判例,无疑非常必要。
最后,在笔者所主张的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中,将未经合法授权的监听、采样、通讯截留也作为排除范围,那么,哪些情况属于合法授权的问题,则是现行中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解决的问题,而这些取证手段在实践中却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未来的立法中,这些问题也应当统筹考虑。
【注释】
{1}郭志媛:《刑事证据可采性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SeeMirjan R. Damaska: Evidence Law Adrif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