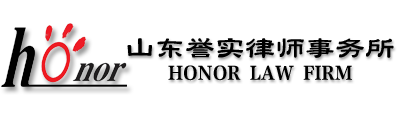[内容摘要]证人作证是对于诉讼证明体系的一种制度挑战,在于从证据信息传递和采纳的路径可以得出直接言词作证的必要性,而从诉讼效率和诉讼实务的角度则会选择书面化作证。基于证据距离和法官认证的惯性的考虑,现阶段较优的证人作证形式,应当允许多元化作证方式的存在。
[关键词]证人 作证 书面化 口头化
一、证人出庭作证的诉讼机理
(一)证据信息传递:证据距离观
在证明的意义上,证据证明信息传递的有效性需要从两个层面进行考察,首先是一个证明信息源的强度问题,即该信息与待证明事件或者行为本身的距离,离案件源头越近,则这个信息本身在真实意义上的可信度就越强;第二是作为信息裁判者对于该信息的观感度,即受众者对于该证明信息传播的承认程度,如作为证人的品格可信程度,其在作证时候的阐述的方式以及现场的反映等等。就第一个层面而言,案件的信息源要求证明信息的生成同案件事实之间的最短距离,即证据学意义上的在场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诉讼法的论证,更多是从举证责任这个角度分析的。借用日本教授石田骧在论述举证责任确定的思路--证据“距离”的观点,依据实质性考虑的主张,只有案件在场的人对于案件具体的情况最为清晰,只有事件文书的人最容易进行这种举证。①
因此,必须要求案件事实的亲历者或者可能的同所要表示的证据资料最为接近的人,直接进行相关的证据信息陈述,才能够在证明对象的意义上,实现对于真相最为可能完整的揭示。
(二)证据信息形式:直接言词原则
要求证人出庭,还涉及到直接言词原则这一基础原理。从证明过程来看,学者认为,不同的证据方法影响着对证据本身真实性的考虑,比如对于证人要考虑其态度的真挚性、观察的准确性和表达的贴切性。②直接言词原则,要求证据的载体必须借助在认识意义上最为直接的“当场人”的描述,除了前述的最近证据距离,可以周全整个诉讼认识的制度设计,为质证的全面展开提供询问对象的基础。这样建构出的互动性的证据形式,能够为上述的证据的调查提供考察的途径。而证据资料一般是作为通过证据方法表现出来或为人所了解知悉的内容,因此,证据资料仅仅是作为一定既知的事实而出现在诉讼中的。明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看待采用直接证言方式而揭示的证据资料的价值,其能够还原出更加直观的事实样态,而非自由裁判者自行借助证据直接去了解。裁判者在这个证据认知采信的过程,需要针对证据资料反映的既知事实的特点,在既知事实和案件待证事实之间,构建其推定逻辑是否成立的联系性确认,并评估证据从已知到未知推断作用程度的证明力或者证据价值。[2](p165~166)
(三)证据信息采纳:经验主义
从裁判者的观感度出发,证据信息是否发生法律意义上的证明作用,在于采纳这些案件信息者的感受,具体到诉讼的场域,就是案件裁判者对于证据信息表述者及表述方式的判定预接纳程度问题。分述到不同的裁判者形态(区分为专业化的职业法官形态和常识化的陪审员形态),对于职业法官而言,借助证人作证的直接言词原则而构筑的直接证据形态,以及借助传闻形态(如证人证言书面化)而构筑的准“直接”证据形态,均会在法官的心证中存在一定预判。特别是对于传闻证据形态而言,即使我们承认这种传闻化“转述”(从口头到书面)的无损耗, 法官群体本身也会对于这种传闻证据预先设定了采信的“折扣”,即所谓的比例证明力的问题,③)当然,在摒弃了如同数学计算的法定证据主义之后,借助法官自由心证的综合,这种折扣只会在拥有不同经验程度的法官视野中,才会潜移默化地发生对于确认证明力大小的作用。
二、我国证人出庭作证价值的实证分析
传统的方法论认为,评估一个制度的价值,主要在于从应然层面的透析,比如对于终极的价值目标的实现,如证人出庭所能够达到的一种对于案件真实的发现深化的助益,这也是目前学术界分析此类问题所惯常采用的思路。但是,这种分析往往会存在一个“理想”与“现实”的差异,即一项制度的应然价值,会被现实中的具体操作流程所异化,而走向另外的反面。比如,证人出庭作证会存在一个由谁提出证人的问题,如果交由纯粹的当事人提出证据,则首先可能存在一个证人作证的利益化取向问题,从而使得作为证人提出的证据是片面性的,这在证明的意义上并不利于真实情况的披露。即使在考虑到诉讼双方的对立性问题,但是一个诉讼真实并非是仅仅存在两面性,而可能是多面的,这就是单纯的对立性所无法全部涵盖的。其次,还会因为当事人提出证据的实质能力而不同,而导致证人在提出时候的无力化情况,这种情况在强调证人作证补偿的制度安排中显得特别的明显。从应然的价值判断,只能指引一定的制度设计方向,但是纯粹的应然化考察,则必定会在实然的层面削弱证人作证的应然效果。
以证人出庭作证实证研究的具体数据来看,⑤在作为样本年份的五个基层法院判决结案的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比率分析:2001年度法院最高的出庭率仅为7.9%,最低为4.9%,平均出庭率为6.4%,加权平均出庭率为6.7%;2003年度最高的出庭率仅为14.6%,最低为9.8%,平均出庭率为12.3%,加权平均出庭率为12.8%;而对比的一个数据组是,2003年度前述样本法院中的四个法院书面形式证人证言的最高出现率高达39.2%,最低出现率也为29.3%,平均出现率为33.7%,加权平均出现率为32.9%。另外的研究数据,也类似地得到的相同的数据情况,参见下表(三个法院2001-2003年证人证言及出庭情况[5]):
E法院 F法院 G法院 合计
案件数量(件) 87 88 75 250
证人证言(份) 172 31 51 254
证人出庭(人) 4 2 3 9
证人出庭率 2.33% 6.45% 5.88% 3.54%
我们观察到,2001年和2003年度作为考察的样本年份,研究者的目的在于探测在最高院《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原则上禁止接受书面证言,并严格限定了职权调查范围的情况下,对于证人实际出庭作证,实现直接言词原则的影响。但显然,现实司法操作在一个相当低的比例下“控制”了证人出庭。如果我们结合职权模式下法官的诉讼进程控制权分析,就可以说证人出庭率低主要取决于法官意图本身。理由在于:诉讼法一般规定了作证义务,并且配套有相关的不作证惩戒措施,如果在司法资源充裕的情况下,则要求证人出庭是非常简单的,如拘传;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法官在考量了即有优先司法资源的情况下,首先并不倾向于如此,而且证人出庭并不能达到其对于探知案件真相的目的,而且因为证人即席作证需要面临着来自双方当事人以及法官自身的询问,会使得案件显得及其冗长,庭审也将极度拖沓,这不利于完成法官的日常工作量要求(或者说要支付更多的工作时间精力)。一言以蔽之,在法官的心目中,传唤证人出庭作证的“性价比”太高,因此有决定权之法官会本能地控制证人的出庭。
从当事人的视角看,要求证人出庭的难度也是很大的。因为证人必须付出一个完整的审判日时间,加上传统的厌诉心理定势,使得如果出庭作证的物质和心理补偿不是足够丰厚的话,出庭作证实在是勉为其难。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证人的当事人进行大量的动员以至于私下补偿(需要注意的是,这是违法的),才可能换得证人出庭。正如前述分析所表明的,此时的法官又会因为是当事人自身提出的证人,而在心理上已经“折扣”了该证人证言的效力。另外,民事诉讼的对抗式构造,要求当事人对于证人进行有效的质询,此时,需要有专业高水平的职业代理人才能够有效胜任。而双方当事人不同的经济实力和他们所具有的程序经验,如质询证人的能力,口头证词和交叉质询制度在挖掘证据之欠缺等,会妨碍了整个诉讼的实质平等实现,虽然这种诉讼对抗的外观具有形式的平等。⑥
三、证人证言的书面化分析
前述分析的数据情况恰恰说明,尽管证人作证对于诉讼真实的发现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样本中证人出庭和书面证人证言两种方式总和,两个证据形式的加权平均出现率高达45.7%),但实际上也存在着最高人民法院政策的强势引导,书面作证方式依旧是我国证人作证方式的主要模式。因此,我们考察此本题的重心,应当回到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这种书面证言方式的盛行,也兼回应证人不出庭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的问题。
(一)书面证言的必然性
从核心的问题来看,证人证言这种证据形式,在我国司法政策以及审判实践长期以来并不扮演主要证据的角色作用,例如最高院《证据规定》第77条第(二)款就规定:“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诉争,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诉争、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在前述的实证调研中,证人证言极少成为案件中惟一的证据种类,绝大多数情况是同其他种类的证据(尤其是书证)一起出现,证人证言在法官形成对案件事实的判断时也较少具有决定性作用,在更多场合只是发挥辅助其他证据的作用。⑦⑧⑨⑩6]( p203)事实上,造成这种“辅助证据”角色是一种遗憾的错位,因为证人证言通过直接言词途径所表现出的现场感和可以即席验证性,恰恰是能够大大优于诸多“哑巴”证据形式所能传递出更为丰富和纯粹的信息。证人的角色就如英国学者罗纳德.沃克指出的:“证人只就其直接感验的事实作证,”○7这种直接感验的特点,显然是有利于直接对于案件事实进行第一性的甄别断定。而交由书面方式的形成,会因为书面转载的“第二手”特点而必然带有“加工”后的痕迹,再加上后续识别理解的又一次“附加”认知,势必造成同原始证据材料信息的进一步隔阂。显然,如果证人仅仅提交书面证言,则对造一方势必不能形成有效的质证,而只能在书面文字表述去寻找漏洞,如果出现机械事实的争执,要么是不了了之,要么是择日补充新证言,徒麋时间,不有利于案件真实被深入挖掘。由此,重塑直接言词方式下的证人作证形态,会在实质意义上增进裁判者对于证人证言的观感,优化其采信的价值。但是,我们在发现其应然价值的同时,也需要具体梳理一下在我国为什么证人不出庭,而转向书面证言的具体原因。
(二)证言书面化的原因分析
为什么我国会出现证人证言书面化的倾向,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证人证言的采信率低。既然采信率低,而把当事人带到法庭却需要很高成本,因此当事人及律师不愿直接促使证人出庭,而将书面证言作为向法院提出证人出庭的理由,若法官对书面证言初步认可,再申请证人出庭。这种操作是比较普遍的惯例。这种操作在证明的意义上,存在着更为显现的一种因素,就是在于证人出庭同法官认证的心理预判有关,即证人出庭更可能给法官造成其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印象,而导致法官警惕性提高乃至“前见”加重而影响证言采信。
第二,书面情结对于认证采证的影响。对比于口头证言方式,书面形式存在着更加固定化以及容易被检索和印证的特点。然而,从案件事实认定的司法习惯看,法官倾向于采用更具有稳定性的证据,以求将案件办成“铁案”。这种传统采证心理,使得具有文本意义的口头证言,更加容易被法官所接纳。我们还注意到,这种文本化的操作具备有较高的节约诉讼成本以提高效益的可能。因为如果更多地纳入口头化作证的方式,则证人由于对案件的了解程度不同,以及在诉讼场域中对于法律语言的认知困难,会出现答非所问或者喋喋不休等情况,使得整个的庭审因此冗长拖延,法官也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应对以及控制这种情况下的诉讼进程。比如加拿大2003年以促进当事人接近司法的改革实施三年之后,从对比数据分析,在1981年,仅仅需要35,000小时的聆讯时间就能够处理51,985件案件,而到了2005年,就需要41,173个小时才能处理21,157个案件。⑧这就说明了必须限制采用直接的证人在证据开示阶段作证的形式,才能实现对于诉讼流程的快速推进。同时,口头证言也可能引发类似于英美法系的当庭质证形态,复杂的质证规则以及主询问(chief examination)和交叉询问(cross examination)的次序排列和限制,会使得口头作证的证言基本上很难被有效的采信。毕竟,建立在攻击意义上的交叉询问,更加容易进行也更容易造出“破绽”。这就使得案件经由复杂繁琐的口头询问之后,难以达到辨识案件真相的作用,反而会带来对于真实的混淆或者无助于诉讼真实的发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往往选择回避证人口头作证这个“烫手的山芋”。
第三,从证人的角度出发,很多证人存在不愿出庭的抵触心理。其一,诉讼进程极其冗长复杂,要求证人出庭往往会耗费其大量的正常工作时间,而此时给予的证人补贴相比较而言也是远不足以弥补其损失的,这样进入诉讼有点得不偿失;而采用书面化就不会耗用过多庭审时间,同时还有作证时间选择的自由。其二,中国证人传统的厌诉心理,进而波及到进入诉讼场所的心理。因此,进入法庭去作证,即使同其没有直接的诉讼利害关系,但是其心理的症结也是抑制其参与出庭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日渐复杂和严肃的庭审构造,使得证人在作证预期中,往往会觉得面对着严厉的措辞询问而处于尴尬的问答状态,因此,使得证人的抵触心理加剧。然而,书面作证则避免了这种直接的场所介入和庭审方式,使得其仅仅面对单向的提问--答问方式,非法庭化的非正式空间作证,也使得证人感受到空间意义上的自由感。
第四,由于证人对于案件的知悉,其往往处于一种类似于布莱克提出的“熟人的距离”之中。这种熟人距离,令其在作证,特别是作出不利于其“熟人”之当事人的证言时,会存在心理顾虑,因为毕竟中国的民众尚未养成关于作证义务的常识认知,而是以所作出的证言效果来评价证人本身。这种证言效果与证人“品格”一旦建立了联系,在具体的作证环境中,特别是当事人直接面对证人的空间下,证人往往会推诿而私下写一个证明或者进行询问,不少时候他还是勉强会做的。⑨
四、证言形式的多元化:一个纠纷解决的视角
无论是证言的口头方式确定抑或是证言的书面方式出具,其展现出的现实司法操作的摇摆,往往被很多持有纯粹程序正义(pure procedure justice)观点的人嗤之以鼻,因为弹性的方式,会导致在纯粹的程序安排中,可能会出现对于提出证言一方当事人的不公正,如一方的证人到庭接受质询而另外一方却是庭外的书面证言。但是,从更为宏大的角度来看,现代化的法治并不必然是以单一的国家权力及其价值观(国家意志)为基准的法律规则之治,多元化的价值理念、多元化的行为模式以及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将会使得现代法治更富活力。[9]( p7)因为,民事诉讼政策的考量,更多应定位于纠纷的解决结果上,而非在这个过程中具体的形式本身(当然,这是一种互相兼容互动的过程)。
(一)证言多元化的诉讼分析
多元化的证言提出形式,可以促进当事人和证人更加活化整个庭审的流程。因为,对比于物证和书证的确定性而言,证言因其主体对于案件事实的认知程度、主体表述案件事实的能力以及证言形成的地点、方式和途径等而充满变数。此时,对于充满对立感的双方当事人而言,借助证人证言这一平台(无论是何种形式),均可以实质性地参与到庭审过程中。因为证人及其证言所呈现出的常识化表述态势(当然,专家证人证言是个例外,但这也恰恰就是有的国家如德国将其排除在证人证言之外的一个主要原因),可以充分满足当事人对于诉讼流程本身的控制感和介入感,这是保障当事人对于诉讼结果正义化评价的关键所在,也是凸显诉讼对抗性、发现真实路径的要求。
在诉讼代理越来越职业化的今天,全方位的法律服务需要借助一些机会和平台去呈现诉讼代理的价值,以更大程度上寻求发挥的诉讼空间和对象。我们认为,提倡证人及其证言在法庭上的出现,有利于营造法律代理人的“用武之地”,从而促进庭审的专业化发展。当然,在无法提供法律代理人的诉讼之中,证人证言的出现会显得更加有必要,因为常识化的证人证言形态,才能够使得无专业诉讼能力的一般当事人,能够直接去辨识对其有利或者不利的证据,形成对于诉讼进程的实质性了解。这在证据的层面,促使当事人在庭上的角色的回归,而避免出现“沉默者”状态而在诉讼场域中显得可有可无。 因此,无论何种形式的证人证言,其法庭上的出现可以促进当事人形成有效的参与满足感,实现当事人到庭的参与性统治(Participatory Governance)的程序正义。⑩
另外,在制度上讨论是否存在单位证人的争议时,应当可以允许存留一个制度的路径,使得如果后续支持单位证人出现的情况下,能够交由单位书证的方式来完成单位证人作证的情况。此时,证人证言的书面化就有其存在的必然价值。
(二)证言形式的提出控制
至于证言具体在诉讼中出现的形式,则可以交由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原因在于,法官作为纠纷解决的“专业”人士,其具备识别一般纠纷争议中证人证言的证据效力和价值,由其在具体的个案情景中进行甄别,即符合目前的庭审职权构造理论中法官推进事实真相发现的形态,有能够契合法官案件管理和进程控制的效率要求。而在民事诉讼的视角中,虽然我们也承认当事人的举证是一种权利,但此时是否以及应否提出什么形式的证据交由当事人自治,则难以在制度上施行。主要理由是如果自治,势必要求合意一致才有进行的可能;但是当事人的对抗式心态,往往使得证据的交锋是必然的,那么最终的合意证言证据提出形式,还是会被架空而走向不确定性的利益博弈中。而此,显然同诉讼真实的这一准则相左。
当然,有担心认为,随着我国审前程序进一步的完善,关于证据的庭上出示,实际上已经被前置到审前,特别是关于证据形式的问题,应当是在庭审之前已经固定化了。这个时候,如果一味强调交由后面庭审的法官再去裁量证据形式,则存在一个要么是事前介入的尴尬,因为这势必造成法官对于案件形成预判;要么就是临时变动带来的庭审程序进行不稳定以及拖沓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应当放诸在我国审前制度到底如何改革建构的前提下讨论。如果走向审前法官和审判法官的角色分野,则判断证据形式就可以直接交给审前法官来做出且无所谓的“预判”污染之可能;如果制度朝向角色的重合,不进行前述的设计(因为可以令审前阶段的法官扮演调解人角色等其他制度安排),则我们认为还是应当坚持审判时法官对于证据形式的“复原”职权,即将本在审前程序固定的书面证言,依据庭审中的特殊变化而引入证人。这一安排的价值在于,虽然可能引起了程序稳定性的破坏,但是一般从概率上看,这种情况并非常态。法官自己掌有是否“复原”的权力,由其依据实际情况来控制。而且,目前法官的很多做法,就是先行审查书面证言,再依据其是否有必要而提请证人出庭。这一制度设计。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于这种操作习惯的一种确认。
实际上,引入法官对于证人证言形式的控制,是基于诉讼模式安排的考量。因为前述当事人的参与正义的外观表现也是同诉讼模式相互协调。民事诉讼的协同模式的框架下,要求当事人与审判者协同互动,优化职权--权利配置,以更好地解决纠纷,实现诉讼社会价值。[11]( p83~88)而确认证言形式,也是这种协同互动的一个特殊的契机,在于法官行使其对于案件推进的能力。这是一种基于诉讼效率(书面化快捷于人证化)以及证据的真实性(书面转述是传闻化的体现)和程序实在化(对人证的质询强度高于对于书面证言的质询强度)的博弈,简单要求在一个证据制度中就去明晰这么复杂的内涵和涵盖千变万化的案情,实在是不合理。事实上,我国民事证据法关于证人证言的界定,重心应当是调整在如何确认包括证人和鉴定人在内的诉讼参与人,也有为诉讼真实发现和程序进行履行义务的要求和惩戒上,至于具体作证的方式,则可以交给法官依据案情来酌定之。由此看来,讨论证言的形式问题,更大的价值还是在其证明力的强度上,而非这种形式本身的正当性。
参考书目:
① [日]谷口安平:程序的争议与诉讼(增补本)[M]. 王亚新.刘荣军.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②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③程春华: 民事证据法初论[M],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④王亚新: 证人出庭作证的实证研究[Z] //王亚新等. 法律程序运作的实证分析。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⑤徐昕:法官为什么不相信证人(讲座稿)[EB/OL],(2006-9-27)。[2007-3-24]. http://cjs.fyfz.cn/blog/cjs/index.aspx?blogid=150927。
⑥[美]迈克尔.D.贝勒斯:程序正义??向个人的分配[M], 邓海平,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⑦陈一云:《 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⑧Francois Rolland, Access to Justice: 3 Years after the Reform of the Code of Civil Procedure[C/OL] , (2006-5-1)。[2007-5-20].http://cfcj-fcjc.org/docs/2006/rolland-en.pdf。
⑨范愉: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⑩陈瑞华:通过法律实现程序正义??萨默斯“程序价值”理论评析[Z] //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11田平安.刘春梅: 试论协同型民事诉讼模式的建立[J]. 现代法学, 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