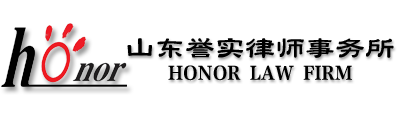近年来,未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等恶性案件频发,引发社会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强烈呼吁。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此作出回应,在刑法第十七条增加了一款,作为第三款,允许对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涉嫌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严重残疾且情节恶劣者,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代表刑法在一定程度上正试图重新平衡维护低龄未成年犯罪者的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平正义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在遵循立法“个别下调”原则的前提下,如何精准适用该条款以平衡打击犯罪、回应民意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关系,并为未来刑事责任年龄政策提供实证依据。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作为英美法系特有的司法制度,通过主观“恶意”补足年龄限制,为解决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问题提供了个案平衡创新路径,与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追诉的审慎态度是一致的。
从实体层面来看:“情节恶劣”作为实体要件中最模糊但最关键的要素,需严格解释以实现“例外追责”的立法原意——其并非致害结果的必然推论,而是独立要件,与行为性质、手段残忍性并列,共同构成追责门槛。在司法适用上,应尽可能统一考察认定标准和程序,最大限度避免在司法适用中的随意性。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核准追诉要件的细化
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了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核准追诉要件。以实体要件确定了追诉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的追诉程序,该规定中的罪名要件以及情节要件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递进式的限定关系,后要件是对前要件的具体限缩,在程序上严格遵循了“慎刑恤罚”的理念。
但是对于“主观恶意”的界定问题,现行立法尚未明确规定。基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部分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主观要件认定标准。这一规则主张:“恶意”虽然是一种主观因素,但是在犯罪过程中会通过犯罪行为客观外部化,并成为可以考量的指标。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认为,人格代表了个体内部的身心整合状态,这一状态显著影响着个人的行为和思考模式。同理,犯罪行为也就是犯罪心理的外化产物。笔者认为,考量低龄犯罪人恶意程度的指标主要包括手段的残忍程度、所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严重程度(残疾程度)以及情节恶劣程度。就恶意证明程序来说,首先,需要确凿的证据支持“恶意”的指控;其次,所有证据都必须通过法定程序得到验证并确认其真实性;最后,在综合考量全部案件细节的基础上,对事实的判断应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只有满足以上条件,才能适用于恶意补足年龄规则。
能够在未成年人犯罪特殊性和个案具体情况的基础上考虑情节的恶劣程度,才能保证对低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成为“必须的例外”和“别无他法的选择”。据此,笔者认为对于“恶意”的认定可以从“特别残忍手段”“严重残疾”以及“情节恶劣”三方面入手,客观化考量未成年行为人的主观恶意程度。
1.明确“特别残忍手段”和“严重残疾”的认定标准
对于“特别残忍手段”的判断,可以构建“行为极端性—后果不可逆性—主观恶性深度”三重递进式判断标准。在客观层面,应重点考察手段的非常规性与痛苦持续性特征。区别于普通暴力,特别残忍性体现在对生物体自然防御机制的刻意突破,如系统性破坏人体神经密集区域(如面部三角区、生殖器官等)或采用化学腐蚀、生物感染等非物理性创伤方式。此类行为不仅造成即时伤害,更通过改变人体正常生理机能结构加剧痛苦体验;在主观层面,需建立“认知要素与行为要素的对应性”评价机制。行为人除具备基础犯罪故意外,还需对手段的特殊残酷性存在明确认知。具体表现为:其一,主动选择非常规作案工具或方法(如预先准备强酸、定制特殊刑具);其二,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伤害升级行为(如发现被害人未丧失反抗能力后改用更残酷手段)。另一种“被害人感受说”认为,“所谓故意杀人罪的手段残忍是指,在杀人过程中,故意折磨被害人,致使被害人死亡之前处于肉体与精神的痛苦状态”。
“严重残疾”的认定需突破传统医学鉴定框架,建立“功能性损伤﹢社会性损伤”的二元评价标准。从生物学角度,应着重评估器官机能损伤的不可逆程度,参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确立三级量化指标:基础级(单肢体功能丧失50%以上)、中枢级(感觉/运动神经系统永久性损伤)、系统级(多器官联合功能障碍)。例如,脊髓损伤导致截瘫合并大小便失禁,即构成系统级机能损伤。在社会学维度,需引入“生活重建可能性”评估模型。通过考察被害人职业能力丧失率(如钢琴家手部神经断裂)、社会参与度衰减值(如面部毁容导致社交回避)及持续医疗依赖程度(如终身透析治疗),综合判定残疾的社会危害深度。
2.明确“情节恶劣”的认定
“情节恶劣”是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中所新增设的实质入罪要件。譬如针对十四至十六周岁和十二至十四周岁未成年行为人的规定最明显不同之处在于“情节恶劣”的程度。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前,“情节恶劣”这一概念多被应用于刑法的具体条文作为评判基准。然而,在司法实践的操作中,对“情节恶劣”的解释存在极高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这直接导致了在处理涉及未成年人权益案件时可能出现的执行标准不统一、同类案件不同判决等现象。
综合未成年人犯罪案例来看,“情节恶劣”和行为人的“恶意”存在高度关联。在未成年人实施的暴力性刑事案件中,行为人往往持直接故意心态并具有高度主观恶性,外化在犯罪行为上就可以体现为“肢解”“奸杀”等暴力行为。将情节恶劣运用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解释当中,凸显行为人在案件中的高度主观恶性,能够有效降低“情节恶劣”这一概念的高度模糊性,防止相关条文在司法活动中被不正当适用。
对于“情节恶劣”的认定,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把握。从主观方面来看,首先要考虑以下两点。第一,犯罪动机的卑劣性。犯罪人的行为区别于普通未成年人犯罪的好奇、模仿心理,需存在明确的加害故意。如预谋性犯罪、报复社会型犯罪、以虐待取乐等特殊动机。第二,认知能力的完整性。应当通过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确认其具备完全辨认控制能力。从主观方面来看,需要加以考虑的危害要件包括以下三点:第一,犯罪手段的残忍性,采用特别暴力、虐待、侮辱等方式实施犯罪。如未成年人是否使用刀具连续捅刺被害人要害部位;第二,危害结果的严重性,即是否造成死亡、重伤等不可逆后果,或对多人造成身心创伤;第三,犯罪行为的持续性,即具有多次违法犯罪记录或累犯倾向,显示其人格危险性未因矫治措施降低。
未成年人生理及心理发育尚不成熟的特点,决定了立法对其应有一定的倾斜性保护。从教育、社会各个方面来看,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是受到了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共同影响,致使其形成了错误的价值观,也是案件的受害人之一。因此在追究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时应保持审慎的态度,最起码要保证追究的准确性,只有在确实符合条件时才能运用刑事手段。对于未成年犯罪者而言,刑罚手段更是一种基于保护性质的惩罚措施。我们将惩罚视为保护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作为最末选项,仅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会采取。因此,准确认定“情节恶劣”这一要件,是保障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前提。
基于此原则与我国当前状况以及司法实践的协调性考虑,其运用须极为审慎,始终坚持“以教育为主导,以惩戒为辅助”的基本理念,全面汇集多方面参与者的角色,将家庭监管、社会支援、司法介入与法律责任紧密结合起来,实施多样化的综合管理策略。低龄行为人的极端暴力犯罪在我国的犯罪总占比中比例不高,且与成年人犯罪存在明显区别,因此在诉讼中更应保持审慎态度对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符合法定情形下再启动核准追诉程序,力求个案平衡。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 张宇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