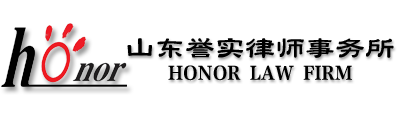| 关键词: 医疗侵权/双轨制/赔偿范围/鉴定方式/赔偿标准 |
|
内容提要: 对于医疗侵权的损害赔偿,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等事项的司法解释存在较多差异,具体表现为损害赔偿的范围、鉴定方式、赔偿标准等都有着不同的规定,由此形成了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的双轨制。这一局面不利于患者的权利保护和维护法制的权威。因此《侵权责任法(草案)》应当对医疗侵权损害赔偿做出更为详细的规定,以解决目前双轨制所带来的问题。
|
|
医疗侵权属于现代侵权法所调整的侵权行为类型之一,而且“一般认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是现代侵权行为法须处理的最棘手的问题。” [1]我国立法机关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在第7章也以专章形式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对于医务人员的说明义务、注意义务、过错推定、因果关系、赔偿责任以及患者的知情权、查阅权、求偿权等内容都做出了较为合理的规定。但该草案对于医疗侵权类型的规定毕竟只有14个条文,对于目前法律适用上存在的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的双轨制并未制定明确、细致的解决方案。因此,在我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完善的过程中,仍有必要对这种双轨制现象进行分析并力图找到解决方案。 一、医疗侵权损害赔偿双轨制的由来
《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了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或死亡的民事责任,这成为法院处理此类纠纷的基础性依据。1987年6月29日,国务院发布了专门处理医疗侵权纠纷的行政法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2002年4月4日,国务院公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将1987年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废止。该《条例》是我国处理医疗纠纷的重要行政法规,其第49条第2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形成了双轨制的根源。2003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规定了《条例》对司法机关的适用效力。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解释》),详细规定了人身伤害侵权赔偿的相关内容,其中关于人身伤害的赔偿标准要高于《条例》的标准。
上述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在涉及医疗侵权损害赔偿时,对于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鉴定性质、鉴定机构、鉴定标准、赔偿标准、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两套不同的规定。 [2]对于同一个问题,有人主张适用《条例》的规定,有人主张适用《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甚至还有人主张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处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因为“医疗机构在此就是一个经营者,有《消法》所规定的经营者身份……《消法》并未将营者及消费者的范围作限制性或排除性规定,明文医患关系排除在《消法》调整范围之外。” [3]当然,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在《条例》和《民法通则》而不是《消法》中寻找法律依据,因为“医疗行为乃以治疗为目的,非以消费为目的……难以将产品与医疗行为相提并论,因为两者在性质上存有甚大差异,救济方法亦大不相同,尤其是从保护消费者一方而言,很难证明医师犯错。” [4]总之,正是这些规定之间存在的诸多差异,形成了在医疗侵权案件上适用法律的双轨制,从而引发了司法实践和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困扰和纠纷。 二、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
《条例》第49条将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限定在医疗事故的范围内,即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条例》规定的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即对于非医疗事故的医疗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医疗机构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社会各界一直存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条例》中将医疗事故细分为l-4级,包括了所有医疗机构在医疗行为中可能产生的过失、过错及相应的损害后果,事实上“已经囊括了所有的因医疗诊疗过失行为所引发的损害后果责任内容,医疗事故已经成为确定医疗机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专用名词,因此不应当在医疗事故之外还存在因医疗过错行为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的问题。” [5]但司法界一般倾向于将医疗侵权行为区分为医疗事故和非医疗事故的医疗侵权.笔者认为,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不应仅限于医疗事故,而应包括所以医疗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原因如下: 第一,《民法通则》与《条例》的关系属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后者的规定不能与前者相冲突。对于《民法通则》与《条例》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条例》和《民法通则》构成了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因为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因过失致患者人身损害引起的赔偿纠纷,本质上属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原则上应当适用我国的《民法通则》处理,《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其法律位阶低于《民法通则》;但由于《条例》是专门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法规,体现了国家对医疗事故处理及其损害赔偿的特殊立法政策,因此,人民法院处理医疗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时应当以《条例》为依据。但是,对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侵权纠纷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106条和109条规定处理。 [6]有学者认为在法律适用上,《条例》和《民法通则》并不构成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而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民法通则》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布的,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由国务院发布的,显然前者是上位法,效力上优于后者。 [7]笔者认为,在适用法律上,《民法通则》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民事法律,《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两者确实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而不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只能产生于同一立法机关制定的同一效力层级的法律法规之上。《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基于违约或者过错行为侵犯他人人身权和财产权的,都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对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因此,无论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只要是医务人员基于违约或者过错侵犯了患者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都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条例》在效力层级上只属于行政法规,不能改变作为基本民事法律的《民法通则》的第106条的规定,其试图免去医疗机构的非医疗事故类侵权责任的规定是无效的。 第二,医疗事故的概念并不等同于民法上医疗侵权的概念。《条例》第2条医疗事故的概念明显地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做出的,“实际上是对行政责任的界定……在民事法律领域应当用医疗事故损害来描述医疗事故所界定的对象,因为在民事领域注重的不是对行为人所施加的行政管理,而是要求行为人应当尽到法律要求的相应义务以免给他人造成损害。” [8]其将医务人员违反各种卫生法律和规范作为医疗事故的重要构成要件,并将医疗侵权行为限定为过失行为,这些都与民法上侵权行为的概念有所偏差,体现了较浓的部门行政立法的色彩,因此不足以作为民法上医疗侵权的概念。 第三,医疗侵权的范围除了医疗事故以外,还包括诸多非医疗事故的侵权行为。事实上,即使不属于《条例》规定的医疗事故,只要医务人员的医治行为造成了患者的权利受损害而没有合法的免责事由,都属于侵权行为,都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为“医疗损害不只是患者生命健康的损害,它是指因医疗行为引起的对患者不利的一切后果和事实。” [9]只要是实施医疗行为的过程中构成了对患者的侵权,医疗机构都必须承担侵权责任,而不管侵权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因为构成医疗侵权的行为除了医疗事故以外,还包括虽然没有直接侵害患者的生命健康权,但却对其自我决定权、隐私权和名誉权等造成了侵害的情况,以及造成患者发生错误受孕、错误出生等情况, [10]这些侵权行为同样足以致使患者承受财产损失和精神痛苦,医疗机构都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不能根据《条例》的规定而自我免责。 三、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的鉴定方式
医疗行为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职业行为,医务人员都是经过职业化训练的人员,不少学者都将医疗侵权归入到专家责任的侵权类型之中,因为“专家主要指律师、公证人、医师、会计师、建筑师等。” [11]在医疗侵权纠纷发生时,对于医疗过程中注意义务的判断、侵权行为的发生、过错的认定、因果关系的判断等等,都需要由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进行认定和判断,因为“当案件所涉及的科学知识高度专业化甚至是深奥难懂时,专家证人便将扮演重要角色,对此并无多少争议。” [12]所以,在医疗侵权纠纷中,进行鉴定是有必要的。 医疗侵权行为被《条例》区分为医疗事故和非医疗事故两类,对于前者,《条例》规定在发生纠纷之后,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交由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而对于非医疗事故的医疗侵权行为,当事人要求鉴定的,其方式为申请法院进行司法鉴定。司法鉴定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和《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的规定来进行,其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组成与医学会的鉴定都不尽相同。
由此,对于医疗侵权行为便存在着医学鉴定(医疗事故鉴定)和司法鉴定(医疗过错鉴定)的双轨制。而这两种鉴定方式在鉴定的启动、鉴定人员的组成、鉴定的方式、鉴定的内容、鉴定的监督等方面都不尽相同。从实践来看,医学鉴定是认定医疗纠纷是否属于医疗事故的必经程序,也是卫生行政处理医疗事故必经的环节;但是从诉讼的角度来看,司法鉴定又确实优于医疗鉴定。 [13]这些差异一直造成医疗侵权鉴定实践的混乱。一方面,当医疗机构希望尽量减少赔偿费用时,“无论其医疗过错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均会极力主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并要求适用《条例》处理以追求最低限度的赔偿或不予赔偿” [14];另一方面,当医疗机构希望避免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时,又希望法院对纠纷采取司法鉴定的方式,以避免医疗事故的认定。而与此同时,医学会组织鉴定的专家都是医疗行业的专家,存在行业庇护的可能性,其做出的鉴定结论对于患者而言公信力不足,而且患者为了得到最大范围的赔偿,往往不愿意接受医学鉴定的结论而申请法院进行司法鉴定,以便要求按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确定的赔偿标准进行赔偿。如此,医学鉴定在现实生活中便处于尴尬的境地,经常成为当事人力图回避的鉴定方式,其存在的价值便大打折扣了。 在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的纠纷中,专业鉴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一般情况下,责任认定和因果关系认定方面的专家鉴定,对于医疗事故诉讼的结果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15]因此必须改变目前鉴定双轨制的状况,建立统一的、具有高度中立性和公信力的鉴定制度,科学设计鉴定人选和监督制度。鉴于目前《条例》规定的由医学会组织医学专家进行鉴定的方式在公信力上遭到了人们的质疑,所以对于医疗侵权纠纷统一由法院来组织司法鉴定的方式更为合理一些。在司法鉴定中,鉴定人作为专家证人主要是对案件中的成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做出专业判断,其应当在鉴定结论上签字,对于鉴定结论有不同意见的专家应当在鉴定结论上注明其不同意见。鉴定人员在必要时应当出庭参加庭审质证,并对其做出的鉴定结论承担法律责任。 四、医疗侵权损害的赔偿标准
总体而言,在各项赔偿标准上,《人身损害解释》普遍要高一些,而且规定得更为详细、合理,《条例》的赔偿标准要低一些,而且许多内容规定得较为简单,尤其是对于患者的营养费和死亡赔偿金两项,《条例》完全未作规定,这对于患者的康复和患者继承人的权利保护都是不利的。然而,对于《条例》对医疗事故的较低赔偿标准,学界也是见仁见智。例如,有学者认为医疗事故赔偿的赔偿标准低于国家赔偿和一般的民事赔偿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医疗机构对医疗事故受害人予以赔偿,实际上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对受害人的赔偿最终还是要分摊在所有的患者身上,而不是由国家出资赔偿。对此,在审判实践中应当适用新《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判决案件,是有根据、有道理的。” [16]也有学者认为《条例》的赔偿标准是不合理的,“关于赔偿费用的计算,《条例》实行的有限赔偿原则,并再一次表现出作为行政法规比较偏重于保护行业利益的缺点。” [17]现实生活中,患者及其家属在医疗侵权索赔中一般都希望能够通过《人身损害解释》而不是《条例》的赔偿标准来获得赔偿,因为前者的赔偿标准明显高于后者,而且赔偿项目也较后者为多。在实践中,“条例规定的事故赔偿标准和民事赔偿标准存在明显的差距,仅死亡赔偿金一项,在中等经济水平的城市,可相差20万元左右。” [18] 如此则形成一个悖论:同一个医疗侵权行为,如果作为医疗事故来处理,那么按照《条例》的标准,患者只能获得较低的赔偿;而如果作为非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侵权行为来处理,按照《人身损害解释》的标准,患者则可以获得更多的赔偿。实践中的一个案例是,某医院手术医生用导尿管时刺破两患者的输尿管,一名患者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另一患者则直接提请司法鉴定,按照非医疗事故处理。结果是前者按《条例》的规定仅获赔3万多元,而后者根据《人身损害解释》的赔偿标准,获赔14余万元。 [19]相同的损害适用不同的法律之后竟出现如此巨大的差距,这不仅难以使患者的权利获得周密的保护,而且有损我国法制的权威和公信力。如此导致的后果,就是“患方对此很不理解,认为《条例》不公正,所以尽量不以医疗事故为由起诉,或到有关部门静坐抗议,或尽量以人身损害为由起诉。” [20]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医疗侵权行为中受损的患者应该获得更多的赔偿,因为他们在此类侵权行为中往往是人身权受到侵害,而对于人身权的重点保护则是民法的应有之义。此外,对于患者精神损害和可得利益损失的赔偿标准也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提高。
当然,从实际社会效果上也并不能将医疗机构对患者更高标准的赔偿责任简单地转嫁到医务人员身上,否则将会导致医务人员为了回避赔偿的风险而大量采取保守治疗的做法,因为保守治疗意味着“可能承担责任的风险迫使医生们采取一些并非医学上必须或合理的措施。” [21] 五、建议
傅利曼曾言:“侵权行为法的核心及灵魂,是有关人身伤害(personal injury)的法律。” [22]尤其是到了现代,因医疗侵权而遭受人身伤害的案件数量不断上涨,在发达国家,“根据美、英以及加拿大等国的调查,医疗事故的受害人数超过了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数,或者至少与交通事故受害人数相同。” [23]虽然目前我国各类侵权案件中,以道路交通事故所致的人身损害最多,但可以预料在将来医疗侵权所致人身损害数量定会不断增加。目前我国在医疗侵权损害赔偿方面存在的双轨制,严重影响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有损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对此,一方面应当修改《条例》,改变其与《民法通则》及《人身损害解释》相悖的规定,取消其对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的事项应当属于基本民事法律的内容,由行政法规对此做出规定是不妥的,尤其是“在某些行业、部门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冲突时,一些部门和监管机构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而是充当这些行业、部门利益的代言人和卫道士,通过制定各种法规、规章和规定,将不正当的行业利益、部门利益‘合法化’。” [24]这也是《条例》颁行以来一直饱受争议并且被当事人尽力回避适用的原因。国务院应当及时修改《条例》,使其回归卫生行政管理法规的属性,不再对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的具体事项做出规定。另一方面,立法机关应当在《侵权责任法(草案)》中增加对医疗侵权损害赔偿事宜的具体规定,以结束目前这种混乱的双轨制局面。“医疗责任是民事责任的普通法在医疗实践中的应用。它只表现出有限的特殊性。” [25]作为民法典重要组成部分的侵权责任法,应当对医疗侵权损害赔偿问题做出统一而明确的规定,使医疗侵权这一侵权行为类型在纠纷的解决中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进行适用。目前正是《民法通则》对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缺乏具体的规定,才致使行政法规、司法解释染指作为民事基本制度的侵权责任法立法,只有制定民法典侵权责任法时,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26] 目前的《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对于鉴定的机构和赔偿的标准均未做出规定,也没有授权其他部门另行立法的规定。这种粗线条的立法并不可取,其忽略了此种侵权类型中的重要问题,而且也没有与其他部门立法的衔接规定,因此并不能改变目前的双轨制局面。在民法典的制定中,立法者必须“把常态民事关系和特别调整的关系,建立相通的管道。没有这样的‘接口规范’,民法典就不像民法典了。” [27]即便将来的《侵权责任法》为了避免频繁修改而不对医疗侵权做出更多的详细规定,其也必须指明未竟事项的解决方法究竟是授权另行立法还是交由司法机关进行解释,否则仍会给行政机关进行部门立法留下空间,从而有碍实现我国侵权责任法高度法典化的立法目标。 |
| 注释: 作者简介:孟强(1981-),男,汉族,湖北保康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王利明教授主持的200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侵权责任法立法疑难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08JZD0008)的阶段性成果。 [1] 夏芸:《医疗事故赔偿法--来自日本法的启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日]新美育文:“序”。 [2] 参见曹勇:“医疗侵权赔偿纠纷案件审理的法律误区 ——兼议最高法院的通知及答记者问”,载 “中国法院网”,网址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71738. [3] 廖秉静:“医疗侵权纠纷解决的现状分析及其完善”,载《广东医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4] 冯文莊:“浅论医疗及医事法之若干问题”,载《法学论丛》第6期,澳门大学法学院2007年版,第92-94页。 [5] 付敏:“对医疗纠纷诉讼现状的分析与思考”,载《现代医院》,2008年第10期。 [6] 参见王连印:“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答记者问”,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4月12日。 [7] 参见马军、温勇等:《医疗侵权案件认定与处理实务》,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8] 杨立新主编:《类型侵权行为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886页。 [9] 龚赛红:“论医疗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从民法的角度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载张新宝主编:《侵权法评论》(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 [10] 参见龚赛红:《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140页。 [11]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的法典化程度研究”,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12] Alan Merry& Alexander McCall Smith:《Errors, medicine and the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P177. [13] 参见马军、温勇等:《医疗侵权案件认定与处理实务》,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 [14] 钱矛锐:“医疗侵权损害赔偿‘双轨制’法律适用原则的困惑与反思”,载《中国医院管理》,2007年第9期。 [15] Michael A. Jones:《Medical Negligence》,London: Sweet& Maxwell Limited,1991,P403. [16] 杨立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新进展及其审判对策”,载杨立新主编:《侵权司法对策》第1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17] 张建军:“医疗过错:现实立法与学者意向”,载《法律与医学杂志》,2003年第2期。 [18] 徐晓宁:“我国医疗鉴定双轨制亟待‘并轨’”,载《健康报》,2007年11月15日。 [19] 参见杨元禄:“医疗纠纷陷入‘双轨’尴尬”,载《医院领导决策参考》,2005年第1期。. [20]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3年 缘何遭冷落”,载《健康报》,2006年4月21日。 [21] Michael A. Jones:《Medical Negligence》,London: Sweet& Maxwell Limited,1991,P4. [22] [美]劳伦斯·傅利曼著:《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下),吴懿婷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页。 [23][日]新美育文:“日本医疗诉讼的现况”,夏芸译,载张新宝主编:《侵权法评论》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页。 [24] 张新宝:“行政法规不宜规定具体侵权责任”,载《法学家》,2007年第5期。 [25] [法]帕特里斯·儒丹:“医疗事故责任”,载《“侵权法改革”国际论坛论文集》,全国人大法工委等于2008年6月主办,第45页。 [26] 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的法典化程度研究”,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27] 苏永钦:“超越注释进入立论”,载王文杰主编:《月旦民商法研究·侵权行为法之立法趋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