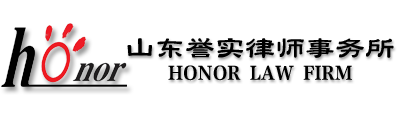【学科分类】商法
【摘要】 业务判断规则是美国公司法发展出来的重要规则,它和董事的注意义务相对,在判断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决策错误责任中,作为注意义务的判断要件,并起到免责事由的作用。在对这一规则的内涵、实施标准、来源、必要性,与侵权之间的区别及其独立存在的原理进行了总结,并对其在组织的公共性维度上的变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中国现行立法存在激励不当和非理性的种种情形。
【关键词】判断规则;注意义务;决策责任;公共责任
【正文】
业务判断规则(business judgment rule),是在美国法上发展出来的,用于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决策是否合理、正当的司法裁量。和大多数国家沿用侵权模式对董事的注意义务进行追究不同,业务判断规则创造了一个具体的免责制度。“business”也可以翻译为“商业”,这对公司等商业组织的判断标准,“商事性”有较好的反映,但对其他组织模式而言,则略为狭窄;“rule”也司以翻译成为“准则”,比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将其翻译为“业务判断准则”。 [1]准则在语感上强调了事后(ex post)法院裁量中做出判断的思维依据的特色, [2]但对其事前作为普遍遵守的规范特点强调不足,反之,规则对事后自由裁量的思维准则的色彩强调不足。 [3]
一、内涵和适用
业务判断规则的表述实际上是不清晰的,普通法的判例中并没有准确和统一的界定,在美国各州立法中也表述不一。立法中最为通用的表述,是1984年的《修订标准商业公司法(Revised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中的8.30(a):董事应当如下履行其职责,包括他作为一个委员会的成员:(1)善意;(2)如同一般的审慎之人在相类似的职位上,在相同的情形下的小心行使职权;(3)以他之理性相信出于公司最佳利益的考量的方式。截止到1999年,美国42个州采用了标准公司法而借鉴了这一表述。 [4]美国法律研究院(ALI)的《公司治理原则》4.01(c)中,则表述为:善意作出业务判断的董事或者高级职员(在如下情况下)视为履行了本节之下的义务:(1)作出业务判断与其无利益关系;(2)做出业务判断得到了信息,而且他也合理地(reasonably)相信在当时情况下作出该判断是适当的;(3)理性(rational)相信,该业务判断出于公司最佳利益的考量。 [5]
在美国法院的判例之中,各州的不同法院在不同的时期,表述也不一。如在特拉华州,该规则并没有明确的立法,依赖于法官在判例中的解释。它在Aronson v.Lewis中的表述为:“‘业务判断规则’是一个推定,公司董事在作出业务决策的时候,是建立在获得信息基础之上的,善意的,并且诚实地相信(belief)所采取的行动是出于公司最佳利益的考虑。” [6]这和很多州的司法实践有所不同,加重了原告的举证负担。尽管表述不一,我们还是可以总结出业务判断规则的要素:善意(in good faith);适时获得了应当得到的信息(duly informed);不具有个人利益(financially disinterested);理性判断或者合理谨慎水平(due care)。
尽管有了要素,但这并不等于规则清晰程度的提高。这些表述大部分都是正向的描述,而不是客观的标准。如何去判断善意,我们可以用“不善意”来界定。而这时候也会存在着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的分野,最后必然是用不存在故意侵害公司利益来具体界定,但这个标准仍然会涉及到故意和疏忽之间的区分。如何去判断信息的获得程度,首先要回答哪些信息是应当去获得的,这只能根据事前决策时候的“应然”标准来判断,并且还要和获得信息的“可能性”相联系。而合理谨慎的水平更多地依赖于理性人的假设,也会存在许多不同的走向。如此之多的模糊地带,表明了现有的业务判断规则的表述仍然是非常不清晰的。 [7]1984年,在重述标准公司法的时候,起草人试图作出进一步的界定,但结果仍然是失败的。他们明确地表示:“我们知道,的确存在着业务判断规则,也知道它是什么和什么时候适用它,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定义它。” [8]
这种表述上的模糊,也是非常自然的,它和公司法的特性是紧密联系的,由于事前的权利界定成本昂贵,需要事后的判例来做出对具体规则的解释、补充和扩展。“公司法的‘血和肉’是法官造法”, [9]企业本身作为一个“不完全合同”、“关系型契约”的结合体,留有非常多的空白。现在的做法是:概括性表述的义务界定了事前所应当遵循的规则,而通过事后个案审查,逐步界定的诚信义务,起到了对明示规则(合同法、章程、股东之间的契约)的空白填补的作用。 [10]
业务判断规则不适用于忠诚义务,如果董事和高管人员在决策中存在着利益冲突,不能援引它来免责。克拉克总结了不适用这一规则的四种例外:如果存在着其它的业务判断相冲突(比如独立董事并不批准交易);管理者的社会或者个人目标;管理者的自我利益;以及特定的法律规则和政策。 [11]不过,基于品德的忠诚义务和能力的注意义务的划分,只是理论上甚至是表述上的清晰而已,“然而很不幸,在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之间并不存在鲜明的界限。” [12]这是因为:首先,行为上的不作为,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公司的损害,常常会出现难以区分究竟是由于品德(私心)还是由于能力(不够尽心);其次,在混合动机的并购行为发生的时候,并不能根据是否存在着自我利益来判断,大部分情况下根据动机来进行判断;第三,在违反公司章程、细则、内部规则的情况下,难以辨别,比如在基于越权行为的诉讼中,对董事和高管人员的免责仍然可以使用业务判断规则。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扩大了业务判断规则的适用范围,就不仅仅是对注意义务的免责,在重合的情况下也可能构成对忠实义务的免责。
注意义务和业务判断规则在方向上是相对的,前者确定了义务而后者明晰了权力,因此存在着重复界定的问题,这在美国法上非常明显。但随着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之间界限的模糊,业务判断规则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尤其是在特拉华州,“(司法中的倾向是)模糊了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的区分。”注意义务和业务判断规则的针对性,在经受着考验。
二、由来和进化
业务判断规则的起源,在美国法上一般认为可以追溯到1829年的Percy v.Millaudon案件。更广义地以对董事责任的免除这一意思来理解,按照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前大法官Horsey的说法,在英国法中1742年的Charitable Corp.v.Sutton案件被认为是今天的“业务判断规则”的始祖。 [13]不过尽管出现类似的判例很早,这些规则并没有引起多少重视。
在19世纪,对董事的注意义务的追究,大多数情况下都局限于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董事,而不会涉及到普通公司。 [14]1850年的Hodges v.New England Screw Co.案件被认为是开始。1940年纽约州的Litwin v.Allen案件是广泛为人所引用的判例之一,Shientag法官确立了今天所使用的业务判断规则。“董事们应当对其履行义务的时候的过错负责。既然不是保险人,董事们并不为判断上的错误,或者从事行为的合理技巧和谨慎上的失误负责。……董事履行职责与否,存在着过失与否(比如违反了注意义务),依赖于特定案件的事实和情形,涉及到的公司种类、大小和财务资源,交易的额度,以及问题的直接程度。一个董事应当根据具体情形需要的召唤来使用其注意和技巧。” [15]
特拉华州法院从1926年的Bodell v.General Gas & Electric Corp.案件中开始确立董事责任,常常会提到欺诈等。一直到1963年的Graham v.Allis— Chalmers Manufacturing Co.以前,并没有明确,董事应当以何种方式来履行职责,尤其是明确董事的注意义务中的理性人标准,而更多地规定善意和诚实信用的目的,等等。这种不明确地界定注意义务和业务判断规则的做法,非但特拉华州,甚至整个美国差不多都如此。一些州的成文法中于1963年才开始界定注意义务,1968年的宾夕法尼亚州商业公司法明确界定了注意义务。
研究表明,在1970年以前,只有很少的案件,并且主要是局限在金融机构之中,董事要对其注意义务承担法律责任。1968年之前只有4个案例,无利害关系的董事在派生诉讼中被认为是违反了注意义务。 [16]在这样的背景下,业务判断规则作为一个单独的规则并没有得到独立表述。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改变,“几乎是一致的倾向,司法并不情愿应用勤勉标准来反对出于好心的,不存在自我谋利的董事和官员。” [17]在Aronson v.Lewis案件中,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将业务判断规则引入到对注意义务的判断之中,并且融合了原有的诸多案例中的规则,明确了其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从此,业务判断规则开始有了独立表述,伴随着股东行动主义、企业兼并浪潮等,不断地扩大了其适用范围。 [18]在1973年到1982年,在156个判例中援引过业务判断规则;而在1983年到1992年,这一数字上升到620个,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业务判断规则的独立,还从法学研究中表现出来,“律师、学者和法官们,为了更新在‘交易年代’的1980年代产生的,以及在1990年代不断涌现新问题的业务判断规则的答案而奋斗。” [19]
与美国法上的业务判断规则不同,英国法在追究董事的注意义务的时候,仍然按照传统,依赖于侵权规则。 [20]1980年代以来,其出现了和美国同样的趋势,加强了对董事和高管人员的保护。 [21]1989年,英国修改了1985年公司法中的310条,允许公司为其董事提供责任保险。这背后的原因和美国一样:第一,来自股东诉讼的压力;第二,企业的兼并和收购活动的加剧。前者使公司的主体性增强,而后者则使公司的客体性增强。公司控制权越来越独立出来,也就意味着职业群体的自由裁量权的价值在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业务判断规则的独立也就是必然的结果。
之所以需要业务判断规则,是因为控制权本身的价值日益独立。随着企业的扩大,公司的社会性、公共性的增强,社会资本的分散化,所有与控制之间的分离程度增大,这带来了不同主体之间,对同一个决策,在不同的时间中的判断上出现了差异,尤其是对公开公司而言,大部分股东并不直接参与经营,公司决策由管理者作出。由于这种独立的管理权力,在公司治理中出现了股东行动主义,股东的派生诉讼在不断增加,股东的监督在英美法中日益成为外部审计之外的最重要的治理机制,迫使法律尤其是法院对此作出回应;同时,随着公司控制权的争夺,公司并购的加剧,公司管理层的防御措施本身带有混合动机:保卫公司和保卫董事和高管人员的自己职位之间难以区分,由此也产生了明确规则的需要,“在我们刚刚结束的时代,空前的并购行为,惊醒了公司法上沉睡了50年的问题。” [22]而业务判断规则,有助于法院避免介入到对动机的考量之中。这样,业务判断规则,既维护了社团的独立性,控制权和自由裁量权的独立价值,以及社团民主和集中决策,也体现出法院对公司内部决策干预上的谨慎小心。 [23]“坚实的业务判断规则……表达了美国法庭的共识决定,以躲避对公司决策事务的干预。如果董事和官员们的决定受到了个人考虑的影响,同时诚意履行了职责……在这一规则的背后是作出决定的理性人的过失假设。” [24]
三、标准和批评
尽管作为对董事责任的保护制度和责任免除制度,业务判断规则的重要性和独立性日益上升,但批评、质疑也非常之多。比如,业务判断规则是不清晰的,且赋予了法院以太大的,甚至是完全自由的裁量权。又比如不同的法院对业务判断规则有着不同的界定,“独立的”、“善意的”、“得到了应当得到的信息”、“有理性基础的”的种种表述,都存在难以界定的特点,等等。按照Gevurtz教授的总结,在实践中美国法院至少存在以下不同标准: [25]
第一,善意标准。当股东追究董事明显失误或错误决策,违反了一般的商业理性的时候,法院却采用善意的标准。“作为对改变中的规则、概念和实践的回应,当新的具体诚信义务的范围,超出了注意和金钱上的自我利益的不足之外的时候,善意就成为一般义务的要求。” [26]尽管存在着冲突的判例,但行为标准界定为善意,似乎是近年来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
第二,重大过失(gross negligence)标准。特拉华州法院在1980年代中期,将业务判断规则的标准确定为重大过失。 [27]在Aronson v.Lewis案中,法院第一次采用了这一标准,“当特拉华州法院在判例中采用很多术语来描述可操作性的注意标准的时候,我们很满意自己的分析,就是董事在业务判断规则中的责任,可以建立在重大过失概念上。” [28]重大过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视为董事和高管人员的注意义务的责任承担认定标准。 [29]但是,究竟什么才是重大过失,在英美法中本身就是非常不确定的、模糊的。按照英国许多法官的意见,“是否有重大过失和纯过失,还是它们仅仅在思想中存在,这确实值得疑问”, [30]“至少到目前为止的所涉及到的私人行动中,重大过失在英美法中并没有被理解。” [31]Rolfe法官认为:“看不出在重大过失和过失之间存在着什么差别,不过是同一种东西的责骂式表述。” [32]
特拉华州法院的界定也不令人满意。1986年的Rabkin v.Phillip A.Hunt Chem.Corp中,采用这一标准对公司的实体和程序决策均进行了审查,重大过失是“不计后果的漠不关心,或者故意的忽略股东的利益……或者没有理由的行动”;但在1988年的re J.P.Stvens & Co.中,则提出对实体决策的审查应当弱于对程序的审查。 [33]
非常有趣的是1997年英国的Armitage v.Nurse案件。法院认为,欺诈和过失(包括重大过失)存在着某种性质上的不同,而在过失和重大过失之间则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这意味着有意的错误行为,对欺诈是必要的,但对重大过失则是不必要的。只有在善意的基础上,才会再去考虑是否存在着重大过失,而特拉华州则将其作为对注意义务(本身要求善意)的免责。
第三,程序审查标准。即主要审查决策作出的程序是否妥当,而对实体决策的合理性审查很弱。按照Gevurtz教授的说法,这一区分来自于对前文已经引用过的美国法学会的公司治理准则中的表述:即董事必须得到做出业务判断有关事项的信息,合理的相信在该种情境下是合适的,但董事仅仅是理性地相信……是为了公司的最好利益。在这种表述下,存在着合理的和理性的的区分,前者是法律中的理性,而后者是个人的理性判断。 [34]
基于这种表述,产生了法院分别对决策中的不同因素予以审查的不同方向,董事和高管人员的决策常常依赖于其他人的判断,在获得这种信息的时候是否充分和合适,这种交易的程序、获得信息的程序应当根据“合理的”标准进行审查,而对决策的判断是否合理等,则基本上不作审查。这在Auerbach v.Bennett一案中非常明显:公司向海外的政府官员和政党做出了有疑问的支付,股东提起针对董事和外部会计师的派生诉讼。作为回应,董事会任命了一个由3名董事组成的特别诉讼委员会,不包括被告,来决定公司应当采取何种策略。委员会在经过了一些调查之后,宣布派生诉讼并不会对公司有什么好处。上诉法院听从了这一委员会的报告,宣布:“特别诉讼委员会……包括两个部分:第一,存在着一个经过选择的程序,符合董事的职责;第二,存在着一个完全的实体决策,根据选定的程序和数据作出,而不是追踪股东在派生诉讼中的主张。对后者而言,实体决策完全是受到业务判断规则的约束,这一判断需要涉及到法律、伦理、商业、推广、公共关系、财务和其他许多类似的因素。由此,特别诉讼委员会得到的结论,超出了我们审查的范围。法院并不能像该委员会那样去考虑种种因素,以及作出决策判断的权重……。” [35]
Gevurtz教授批评这些标准是模糊和冲突的,但问题实际上更复杂一些。上述三个标准,在“不作为”的案件中,几乎会发生重合。“作出了一个坏的决策”和“没有作出一个好的决策”之间的主张,是很容易转换的。重大过失、程序和实体分离的标准,似乎更多地是对“作出坏决策”的审查标准,这可能会被善意标准所吸收。迪斯尼案件就是一个例子,并且被视为是注意义务和业务判断规则的重大变化:善意标准成为特拉华州的新标准。 [36]在该案中,原告追究董事们的责任,因为他们批准了一个有利于Michael Ovitz担任总裁的合同,并且在14个月后允许其正常离职而获得了1.4亿美元的补偿。原告的理由是董事们没有进行任何决策,对股东们不存在善意。2003年,在Emerald Partners v.Berlin中,特拉华州最高法院进一步确认了迪斯尼案中的善意标准。
但善意标准会引发更大的争议:诚信义务究竟应如何划分?善意无论对忠诚义务而言,还是注意义务而言,都是其中的构成要件。“善意标准,特别是放弃职权的情况下……几乎充当了合理注意和忠实概念的桥梁,将可能被视为是对前者的一定违反,转换成为对后者的违反,即便在缺乏相反的财务利益的情况下。的确,如同一部杰作的作者所注意到的,善意义务是董事的合理注意和忠诚的基础义务的共享因素。” [37]如果采用了善意标准,究竟是对忠诚义务的免责还是对注意义务的免责呢?是否意味着业务判断规则的扩大呢?这进一步引发了另外的理论纷争,善意是否应当是一个独立的义务?这可以追溯到1993年的Cede & Co.v.Technicolor,Inc.。在该案中,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宣称诚信义务由三元组成:善意、忠实和合理注意,并且为一些学者所接受。 [38]
法院究竟会走向何处,采用了善意标准是否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还需要我们拭目以待。可以明确知道的是:善意固然得到了强调,但其定义、范围和操作标准仍然需要界定,毕竟这只是对董事的主观状态的界定。标准即便统一在善意之下,至少就目前来看,也仍然是模糊的。
除了对业务判断规则本身的模糊性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批评,这些意见可以归结为价值和技术这两个层面:首先在价值层面上,法院本来之所以要采用业务判断规则,其直接原因在于这一规则对董事的决策进行保护,“法官并不是董事,董事也不是法官,业务判断规则是对这一区分的提醒”, [39]但是,随着其应用带来了另一个局面:法院实际上陷入了事后对董事业务判断的支离破碎的审查。其次在从技术层面上,用侵权法规则本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独立的业务判断规则在技术上有什么独立的价值呢?这两个层面的批评,实际上仍然根源于业务判断规则自身表述上的模糊。
四、价值和技术
就业务判断规则本身的价值层面的批评,也有不同的方向,在公司和股东的紧张关系之中,支持股东的批评这一规则对股东不利,而支持公司的则批评这一规则对董事和高管人员不利。从第一个角度发出的批评,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曾任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Cary教授提出过。现在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第一,该规则大大加剧了原告的举证负担,他必须证明存在着恶意、欺诈或者滥用权利。由于这些举证都是“带有颜色”的,导致负担较重。最困难的是,证明董事和高管人员的行为是出于削减公司利益的目的。 [40]第二,该规则将一个股东寻求对压制性行为(oppressive conduct)的诉讼,变成了非常松散的、形式化的审查过程。这导致了对股东的压制行为的法律规制变得非常困难;追究董事和高管人员决策失误的案件,常常有利于大股东而非小股东,比如工资的确定、公司资产的出售,或者是分红的发放或者形式等,在保护董事的同时,实际上保护了大股东。 [41]第三,在比如合并中的排挤股东等复杂情形中,常常会出现每一个单独的步骤都具有“合理的理由”。比如公司为了扩大经营而和其他公司合并,并将控制权交给别人,而公司合并之后,利润下滑或者公司资产应当出售等,或者另行发行新股将小股东的股权稀释,甚至将其排挤出局。但是这些步骤合起来看,就会出现明显的不当。然而每一个步骤都可能会受到业务判断规则的保护。第四,业务判断规则的案例中总是涉及到利益冲突,常常对控制股东的自我交易视而不见,或者是对其信息的获得程度不加考量。 [42]第五,股东可以通过合同或者章程将业务判断规则的免责排除在外。
不过也有国家的立法站在另一个极端的立场上,比如采用大陆法系规则的印第安纳州对董事责任采用了“热心的,但头脑空空的”(warm heart,empty head)的标准,立法中规定“董事无须对任何作为董事所采取的行动,或者采取行动的失败负责,除非……有意地错误行为或者不计后果的违反或者疏于履行章程。对此,”Branson教授指出,保护董事本身是一个政策性导向,而采用了业务判断规则,反而造成混乱,不如印第安纳州的做法清晰明了。 [43]许多学者都认为,可以废除注意义务,而扩展忠实义务就足以解决问题。 [44]
立法者也不看好业务判断规则,这在一些英美法系国家对业务判断规则的吸收和借鉴过程中也可以看出来。澳大利亚是在英联邦国家之中最早引入对注意义务的法定表述的国家,1989年又重新进行表述(实际上照搬照抄了标准公司法)。但在该国法院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对公司董事的决策进行审查。因为在经过对比之后发现,业务判断规则可能造成对自我交易的免责而不利于投资者的保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992年明确放弃了业务判断规则的引入。 [45]
在美国遭遇到安然丑闻之后,加上股东保护主义的抬头,业务判断规则在各国的延伸遭到了挑战。在许多立法者眼中,与其加强对董事和高管人员的责任保护,不如采用更为严格的程序规定,来加大公开公司的信息披露,更为合理。也有学者站在索克斯法案(Sarbanes— Oxley Act)的立场上,对这一规则进行批评。 [46]
显然,对业务判断规则的独立性,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如何认识这一规则呢?其背后的理性又是什么呢?在过去的认识中,对法院需要业务判断规则的理由,学者们的总结甚多,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评价能力。法官并非经营上的专家,在这种情况下,强行介入对决策的裁量,常常变成“二次猜测”(second guess); [47]事后试图回溯董事和高管人员的事前决策,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业务判断规则反映了法院不愿意介入到对董事会决策理由、过程、依据的猜测之中。“业务判断规则的一个明显标记,就是法院不会替代董事会的决策。” [48]业务判断规则与其说是一个责任规则,还不如说是一个“司法克制”的规则。这不仅仅和法官并非商业上的专家相关,就理论而言,法官本身就难以对组织中的决策做出裁量和判断。无论是哪一种组织,其内部的信息传递、组织结构,以及个人与组织之间的责任切分、认定与追究,原本就不为传统法律理论所关注。 [49]这一原理,对公司法也不例外,有学者宣称,“公司治理的基石是这样一种理念:法院对公司内部事务的干预必须最小。” [50]
(2)因果关系。事前行为和事后结果之间的不一致。决策的合理性和结果的合理性并不是吻合的,结果产生的原因是多元的,因果链条可能很长,从而导致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变远。在既有的案例中,也表现出这种特色。比如Smith v.Lewis(1975)案件,原告在退休计划中遭到了个人利益的损失,但被认定为属于其律师的责任;在Spherex,Inc.v.Alexander Grant & Co.(1982)案件中,债权人依赖于有问题的财务报表而放贷,导致了损失,被认定为属于其会计师的责任;在City of Eveleth v.Ruble(1974)案件中,城市需要重新安装通风口,被认定是工程师的责任。 [51]在英美法中,责任承担的因果关系要求有两个:事实上的原因和法律上的原因,后者也被称之为“最近原因”(proximate cause)。公司董事和高管人员的决策结果可能会受到市场、产品、技术、财产、财务等等多方面因素的干扰,常常会出现“错误的决策导致了错误的业绩”成立,但“没有错误的决策就不会产生错误的业绩”难以证明,前者是事实原因,后者是法律原因。这既 [56]可能是一个因果关系问题,也可能表现为是一个“损害”认定问题,并不是所有的损失都可以被认定为原告的损害。对诚信义务的诉讼尤其如此。 [52]这表现在Mendelovitz v.Vosicky(1994),re Teledyne Defense Contracting Derivative Litig.(1993)等案件之中。 [53]
因果关系和损害认定中的第三个方面,则是“经济损失”问题。由于英美法中认定损害在私法规则中采用了“期待利益”标准,这一标准产生的“鸡又生蛋,蛋又生鸡”的问题自然也就带到了对董事责任的认定之中。基于此,英美法中常常并不保护纯经济损失, [54]在公司决策诉讼之中,许多“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利益”是无法保护的。
(3)风险激励。努力和成果之间,存在着风险,也产生了结果的不确定性。比如A项目投资回报50万,确定100%;B项目投资有95%的可能性获得1000万的收入,5%的可能性为零,期望回报应当是1000×95%+0×5%=950(万),显然理性的决策应当选择A项目。但当5%的可能性发生的时候,则可能会发生股东对董事决策的质疑。而在这种诉讼之中,法官常常只能调查投入,不能调查产出,因此并不能依赖调查最后的结果来推断事前的决策是否合理。 [55]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司董事面临着个人责任,他们就会躲避开风险性的行动,即便这种行动整体上有助于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风险投资一般会具有更大的潜在利润,作为交换,则强化了损失的风险。为什么董事会进入到这样的冒险活动之中呢,如果他们可能被要求从不幸的结果承担一部分的损失,而幸运的结果产生的利润则流向了股东。” [56]
非但如此,对同一个决策总是会有不同的方案出现,在事后来衡量和比较事前的不同决策选择,对管理层而言,会产生不当的激励。
(4)诉讼因素。董事是股东所选举的,股东对其的制约方式是多样的,包括选举、章程、监督机制的设计等。并不是在诉讼中不提供救济,股东就无法得到权利的实现和保护,以及对董事和高管人员的制约。股东也不是被强迫成为股东的,当他对公司管理者的决策不满的时候,可以采用“用脚投票”的权利。 [57]集中的、非民主的决策本来就是社团的本质所在,如果仅仅在股东和管理者的决策意见发生分歧的时候就追究董事和管理者的责任,就违反了社团的多数表决规则的权力行使原则。社团的加总意志本来就是通过“布尔什维克式”的方式形成的,股权是可以分散的,但控制和决策则是集中的,这本来就是企业的特点所在。如果过分地按照某一部分成员的意志来判断正确与否,就会破坏社团本身所具有的特点。
非但社团的本质如此,有限责任的要求也似如此,有限责任使得股东无需同合伙一样,对公司的事务事事关心。有限责任还产生了另外一个激励:大小股东之间的智猪博弈。小股东放弃了管理公司的权力,而取得稳定的收益、多元化投资等等诸多好处。换言之,小股东本身在正向的决策中,并没有积极参与管理,而一旦出现了问题或者坏的结果,就来提出意见,这似乎也是矛盾的。在追究董事责任的派生诉讼之中,真正发挥作用的并不是实际上的股东,而是律师,这又有架诉的嫌疑。为什么一个股东买了一份股票之后,就可以不用付出精力,不参与管理,享有自益而又可以去质疑管理者的决策呢?就公平的角度来说,股东可以通过多元化投资来分散风险,而董事和高管人员则不同,其做出决策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不能分散投资, [58]如果缺乏业务判断规则,也难以对其有效激励。
(5)威慑效果。法律责任的承担本身不是目的,而对社会的激励,进而产生服从的效果,才是法律的合理性所在。在法院的诉讼中,董事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依赖于金钱方式的损害赔偿。是否采用了类似于金钱惩罚的方式,可以解决对决策行为更为理性,更为聪明的激励?不仅如此,公司越来越多地提供各种免责,责任保险,而这些成本本身是公司承担的。这就出现了一个循环:董事被追究注意义务的责任,判断标准是损害了公司利益,而承担责任的时候,则是公司出钱为董事和高管人员上保险。
尽管有这些合理性的论证,不过这些理由并没有解决法律上的技术问题,为什么要在侵权之外发展一个独立的规则,称之为业务判断规则呢?上述理由,同样也适用于任何的职业侵权。它只能解释“免责事由”的合理性,而不能解释独立的业务判断规则存在的合理性。“如非必要,无需增加。”既然董事、高管人员的决策失误,在传统上是采用侵权模式来解决的,为什么还需要新规则呢?Gevurtz从技术上指出:“当决策导致了对其他人的伤害,那么医生、律师或者司机将会发现自己会在基于过失的诉讼中处于被告的地位……非常简单,并不需要对公司董事们的业务判断做出什么特别的对待。那么应当置业务判断规则于何地呢?显然,这是一个作用非常有限的短语,而存在非常大的可能性造成毛病(mischief)。因此,业务判断规则就是这样一个规则,没有它公司法同样运作得很好。” [59]
这种追问的确是非常有道理的,同样是采用判例法模式的英国法,并没有这一规则,仍然沿用侵权来解决。 [60]“公司可以和个人一样基于过失而被诉讼。有限公司的董事,并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是董事就要对雇员的侵权承担个人责任,除非他们需要对已经做出的行为的指示负责,或者怠于作出指示,或者违反了个人的注意义务。” [61]如果说,业务判断规则是对董事责任的免除,那么还不如印第安纳州的法律模式,或者采用各种立法中都有的责任免除立法,也可以作为侵权的免责事由而存在,业务判断规则独立的必要性似乎并不那么强烈,它是侵权规则的同义反复。
五、辩护、理性和借鉴
既然如同美国之外的其它国家实践所揭示的,运用侵权规则来解决公司法上的董事和高管人员的激励、责任问题完全可行。独立的业务判断规则,其存在的理由何在呢?笔者认为,业务判断规则是必要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它,是否独立则涉及到如何理解与传统法律规则的接轨。这其中的理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客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形态、组织结构的变化;以及主观方面的法律技术和法律理论上的进步。
对业务判断规则的批评,我们要看到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侵权模式在解决公司治理中的困难。这从反面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公司法发展方面走在最前面的美国法上会需要这样一个独立规则。这可以从英国学者的反思中得到一个印证,基于侵权的注意义务并没有得到理论上的有效支持。 [62]这既有社会实践中的因素,即股东诉讼较少、公司并购频率比较低、股权不够分散、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等原因,也有学术研究中的因素。
侵权模式的第一个困难在于其核心:理性人的假设。理性人的假设和“预见能力”问题紧密相关, [63]但对它的界定则是侵权法的“谜”。非但如此,其标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注意义务是由普通法和衡平法共同发展的,从历史上看,它建立在不同的注意标准之上,在很多方面并不相同。” [64]以始终采用侵权模式的英国法为例,传统上的标准是由1925年的Re City Equitable Fire Insurance Co.判例确立的,Romer法官在该案中明确界定“普通人在相同情形下处理自己事务的注意”为标准,这基本上是最低的标准,也是重大过失的标准; [65]这种情况随着社会变化而改变,在1991年的Norman v.Theodore Goddard一案中,Hoffman法官援引了1986年破产法上的更高要求。该法规定了两个标准:一是客观的董事本人所具有的一般知识、技能和经验;二是主观的人们对他的期望。这明显大大提高了标准。在澳大利亚的实践中,Rogers法官则采用了更高的“商业性的现实主义的义务”,宣称“最近的观点是认为董事义务的本质就在于董事必须采取合理的措施指导和监控公司的经营活动。董事被要求对公司事务和公司财务变化情况至少有一般的了解,董事应对提交董事会决议的事项有一定的了解并且为独立的判断。” [66]侵权的理性人标准的波动,也反映出这种模式并不比业务判断规则更为清晰。
对董事的理性人标准界定的困难,是因为来自于对董事究竟应当是职业的,还是一般人;来自于其所服务的公司的类型、董事的角色、不同的职能、具体的职位,等等,“没有一个的单独的,想象中更为严格的董事义务可以满足这种多样性。” [67]
侵权模式的第二个困难在于:事后的评价如何作出。侵权诉讼的特点决定了法官、专家或者陪审团需要对决策进行实体性的裁量。而业务判断规则中的程序和实体划分的标准,可以避免法官介入这一判断。诚如William Allen所说,“我认为,不存在这样的合法性基础,如果无利害关系的董事,行为是善意的,对问题采取了合理注意,并且属于董事的权限范围,这种情况下管理公司的经营和事务,要被施加损害赔偿(或者禁令)……将会使得法庭成为超级董事。” [68]
业务判断规则和侵权模式的一个根本不同,在于保护天才的决策。当法官不采用侵权模式的审理方式介入到具体的业务判断的裁量之中的时候,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在于:并不是要去保护愚蠢的决策,而是要保护天才的决策。任何天才的决策,可能在开始的时候都会被视为愚蠢的,而法官不去判断,就避免了采用常人的标准来衡量天才的困境,尽管可能会有更多愚蠢的决策逃脱。侵权的一般人标准也好,普通商人标准也好,常常会像希腊神话中的普洛克路斯忒斯,用法官的智商、认知衡量所有人。
侵权模式的第三个困难在于:没有事前的概念。按照艾森伯格的说法,它不能区分坏的决策和决策的变坏(bad decisions and decisions turn out badly)。 [69]侵权只是考察了义务、过错、因果关系和损害,而没有考虑决策做出的过程和决策实施之间的差异。公司的本质在于社团性,而社团的意志的特点在于程序,是由公司治理所确立的决策过程。业务判断规则实际上属于一个安全港规则(safe harbor),考虑了事前的信息获得,善意状态和决策做出时候的谨慎。
最后,我们当然也可以将侵权模式和业务判断规则结合起来,将业务判断规则看成是侵权中的注意义务下的免责事由,而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但这并不妨碍业务判断规则的独立性,因为无论是注意义务,还是侵权行为,不可避免地要有一套规则来做出具体界定。业务判断规则的模糊,并不比其他规则更过分,相反,它至少为法院从何种角度考虑公司决策问题提供了思路,在这个意义上,将其理解为一个思维模式也是非常恰当的。
其实,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业务判断规则的模糊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董事的职位、个人能力、县体职责、公司特性等等的千差万别,而规则的特性是统一与其之间的矛盾造就了这一特点。这种矛盾,需要在应用这一规则的时候,考虑公司的特性。一个公共性较强的公司,受到业务判断规则的保护就应当更多;而一个公共性较弱的公司,则更需要向股东负责。 [70]
为什么美国法对独立的业务判断规则的需要如此突出呢?为什么其他国家包括英联邦国家并没有采纳这一规则呢?在笔者看来有以下几个原因:(1)市场因素。相对其他各国,美国的股权市场分散,而经理市场发达,造就了独立的公司地位,从而对职业群体的激励提出了需要,而其他各国则缺乏这一背景。这两个市场的发展在全球化下会不断向美国模式靠拢,在这一意义上来说,公司法规则在各国的分布是进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而不是生物多样性的表现;(2)公司治理的因素。各国的历史、文化、制度等等因素造就了不同的治理模式,德国的共同决策机制和主银行制度,日本的相机治理模式和内部人控制,英国对职业会计群体的依赖都不同,而美国则依赖于派生诉讼为代表的股东监督机制,在这种背景下,也导致了对法律规则的不同需要;(3)组织的公共性程度不同。公司日益独立于股东,社团独立于成员,这迫使业务判断规则从侵权中独立出来,也导致了股东和公司对决策不同态度下法院必须发展某种规则应付挑战,在这个意义上,以大公司为主的特拉华州在法律规则的进化上走在了前面也就不难理解了;(4)行为的复合性程度不同。由于资本市场中的兼并收购,不断挑战着传统的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的划分,董事对带有混合动机的并购行为的积极参与,使得法律规则需要一个独立的判断标准,而不是运用传统的规则来敷衍。
那么,在这种不断发展的法律规则和法学理论中,中国公司法中的注意义务和业务判断规则又如何呢?
1994年版本的公司法中,并没有界定注意义务,而在2005年修订的版本中,在第148条中第一次提出了“勤勉义务”的概念,但并没有任何的进一步界定,同样也就很难有业务判断规则的界定。非但如此,勤勉义务究竟是指duty of diligence还是指duty of care也是有待于推敲的。但对董事的决策责任,则在两个版本的公司法均有规定,113条第3款规定了股份公司的董事决策责任,“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对有限责任的董事决策只是第49条第2款要求,“董事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这一规则和注意义务相比,更多指向了遵守法律(obey the law)和公司形式(formality)的义务,强调决策行为的正当性。这和注意义务之间有不同,但也有重叠。这是由于法律和章程常常会采用比较含糊和笼统的表述,具体判断的时候还是需要借助于特定事项是否符合注意义务、是否造成了公司损失来判断。不过,其中的决策责任的抗辩理由,有令人啼笑皆非的感觉,如果董事签名反对了就可以免责,那么在现行的股份公司制度下,董事的最优选择是“反对”,因为不作为、不决策,就无需承担责任。尽管在中国现行的股东控制公司模式下,股东仍然可以更换不作出决策的董事来达到控制和激励的平衡。但如果再进一步考虑我国的诸多上市公司都属于公共性更强的国有企业,他们既不能分享剩余,也不能获得与业绩相关的激励,董事和管理者的行为规则更近似于官员而不是企业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枪打出头鸟”,而什么决策都不作的反而免责,这如何促使管理层有效决策?
总体上来说,我国的模式既不是侵权模式的责任规则,也不是业务判断规则,是僵化的“签名认定标准。”可是即便如此规则,我们还可以从“郑百文”的“陆家豪”被证监会处罚中看到另外一种逻辑:一个人不参与决策,并且实际上不能参与决策,反而被处罚。这种激励将会引导公司去向何方?
【注释】
[1]参见刘连煜:《公司监控与社会责任》,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51页。
[2]Branson教授指出,这一规则更多是司法裁量的技术性思维。See Douglas M.Branson,The Indiana Supreme Court Lecture:The Rule That Isn’t a Rule—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Valparaiso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32,2002,pp.631—654.
[3]也有学者认为存在着business judgment rule 和business judgment doctrine的不同。Manning认为这种区分只是存在于文字上,但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认识。See Bayless Manning,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in Overview,Ohio State Law Journal,Vol.45,1984,pp.615—627.
[4]See D.Gordon Smith,A Proposal to Eliminate Director Standards from the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Law Review,Vol.67,1999,pp.1201—1228.
[5]See Charles Hansen,The Duty of Care,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and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ject, The Business Lawyers,Lawyers,Vol.48,1993,p.1355.
[6]Aronson v.Lewis,473 A.2d 805(Del.1984),p.812.
[7]See Jill E.Fisch,The Peculiar Role of the Delaware Courts in the Competition for Corporate Charters,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Law Review,2000,p.1061,at pp.1074—1075 [8]See Robert Hamilton and Jonathan R.Macey,Corporations:Including Partnerships and Limited Partnerships:Cases and Materials,4th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90,p.703.
[9]E Norman Veasey and Christine T.Di Guglielmo,What Happened in Delaware Corporate Law and Governance From 1992—2004?A Retrospective on some Key Development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Vol.153,No.5,2005,pp.1399—1512,at pp.1411.
[10]See Oliver Hart,An Economist’s View of Fiduciary Duty,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Review,Review,Vol.3,No.3,1993,pp.299—313,at p.301.
[11]See Robert Charles Clark,Corporate Law,Aspen Law & Business,1986,p.136.
[12]Frank H.Easterbrook and Daniel R.Fischel,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orporate La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03.
[13]See Henry Ridgely Horsey,The Duty of Care Component of the Delaware Business Judgment Rule,Delaware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Vol.19,1994,pp.971—998,at p.975.
[14]See Stuart R.Cohn,Demise of the Director’s Duty of Care:Judicial Avoidance of Standards and Sanctions through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Texas Law Review,Vol.62,1983,pp.591—637,at p.603.
[15]Litwin v.Allen.25 N.Y.S.2d.
[16]See Joseph W.Bishop,Jr.,Sitting Ducks and Decoy Ducks:New Trends in the Indemnification of Corporate Director and Officers,Yale Law Journal,Vol.77,1968,pp.1078—1103,at p.1099.
[17]See Supra Note 16,p.593.
[18]See Dennis J.Block,Michael J.Maimone and Steven B.Ross,The Duty of Loyalty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cope of Judicial Review,Brooklyn Law Review,Vol.59,1993,pp.65—105.
[19]See Dennis J.Block,Stephen A.Radin and Michael J.Maimone,Chancellor Allen’s Jurisprudence:Chancellor Allen.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and the Shareholder’s Right Decide,Delaware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Vol.17,1992,pp.785—842,at p.785.
[20]See R.A.Percy and C.T.Walton,Charlesworth & Percy on Negligence,Ninth edition,London:Sweet & Maxwell,1997,p.125.
[21]See D.D.Prentice,Creditor’s Interests and Director’s Duties,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10,1990,pp.265—277.
[22]See Willian T.Allen,Independent Directors in MBO Transactions:Are They Fact or Fantasy?,The Business,Vol.45,1990,p.2055.
[23]See Stephen M.Bainbridge,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as Abstention Doctrine,Vanderbilt Law Review,Vol.57,2004,pp.83—130.
[24]Miller v.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 Co.,507 F.2d 759,762(3d Cir.1974).
[25]See Franklin A.Gevurtz,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Meaningless Verbiage of Misguided Notion?,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Vol.67,1994,pp.287—337.
[26]See Melvin A.Eisenberg,The Duty of Good Faith in Corporate Law,Delaware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Vol.30,2005,p.14.
[27]See William T.Allen,Jack B.Jacobs & Leo E.Strine,Jr.,Function over Form:A Reassessment of Standards of Review in Delaware Corporation Law,The Business Lawyers,Vol.56,2001,p.1287.
[28]Aronson v.Lewis,473 A.2d 805,Del.1984,p.812.
[29]See Lyman P.Q.Johnson and David Millon,Recalling Why Corporate Officers are Fiduciaries,William & Mary Law Review,Vol.46,2005,pp.1597—1653,at p.1631.
[30]Hinton v.Dibbin(1842)2 QB 646,114 ER 253,by Lord Denman CJ.
[31]Pentecost and another v.London District Auditor and another,(1951)2 KB 759,at p.764.
[32]Wilson v.Brett(1843)11 M.& W.113.
[33]See S.Samuel Arsht,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Revisited,Hofstra Law Review,Vol.8,1979,p.93.
[34]See supra note 27,pp.300—301.
[35]Auerbach v.Bennett,47 N.Y.2d 619,393 N.E.2d 994,419 N.Y.S.2d 920(1979),at p.1002.
[36]See Thomas Rivers,How to Be Good:The Emphasis on Corporate Directors’Good Faith in the Post—Enron Era,Vanderbilt Law Review,Vol.58,2005,pp。631—675.
[37]John L.Reed and Matt Neiderman,“Good Faith”and the Ability of Directors to Assert &102(b)(7)of the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as a Defense to Claims Alleging Abdication,Lack of Oversight,and Similar Breaches of Fiduciary Duty,Delaware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Vol.29,2004,p.111,at p.121.
[38]See Hillary A.Sale,Delaware’s Good Faith,Cornell Law Review,Vol.89,2004,p.456.
[39]See Jay P.Moran,Business Judgment Rule or Relic?:Cede v.Technicolor and the Continuing Metamorphosis of Director Duty of Care,Emory Law Journal,Vol.45,1996,pp.339—386,at p.339.
[40]See Ralph A.Peeples,The Use and Misuse of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in the Close Corporation,Notre Dome Law Review,Vol.60,1985,pp.456—508,at p.482.
[41]See F.Hodge O’Neal,Oppression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Protecting Minority Rights in Squeeze—Outs and Other Intracorporate Conflicts,West Group,1985,& 9.04.
[42]See Zohar Goshen,The Efficiency of Controlling Corporate Self—Dealing:Theory Meets Reality,California Law Review,Vol.91,2003,pp.393—438,at p.428.
[43]See Supra note 2.p.634.
[44]See K.E.Scott,Corporation Law and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ject,Stanford Law Review,Vol.35,1983,p.927.
[45]See J.H.Farrar,Corporate Governance,Business Judgment and the Professionalism of Directors,Canadian Business Law Journal,Vol.6,1993,p.1.
[46]See Lisa M.Fairfax,Spare the Rod,Spoil the Director?Revivalizing Directors’Fiduciary Duty Through Legal Liability,Houston Law Review,Vol.42,2005,pp。393—456.
[47]See P.John Kozyris,etc.,Symposium:Current Issue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Conference Panel Discussion: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Ohio State Law Journal,Vol.45,1984,pp。629—653,at p.646.
[48]Unocal Corp.v.Mesa Petroleum Co.,493 A.2d 946,(Del.1985),at p.954.
[49]See Peter Harris,Difficult Cases and Display of Authority,Journal of Law,Economics,& Organization,Vol.1,1985,pp.209—221.
[50]Charles Hansen,The ALI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ject:of the Duty of Due Care and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a Commentary,The Business Lawyer,Vol.41,1986,pp.1237—1253,at 1239—40.
[51]See supra note 27,p.313.
[52]See William A.Gregory,The Fiduciary Duty of Care:A Perversion of Words,Akron Law Review,Vol.38,2005,pp.181—206,at p.183.
[53]See Norwood P.Beveridge,Does the Corporate Director Haw a Duty Always to Obey the Law?,DePaul Law Review,Vol.45,1996,pp.729—779,at p.741.
[54]See Richard A.Epstein,Torts,Aspen Law & Business,1999,p.404.
[55]参见张维迎:《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See also Reinier H.Kraakman,Corporate Liability Strategies and the Costs of Legal Controls,Yale Law Journal,Vol.93,1984,pp.857—898,at p.864.
[56]Kenneth B.Davis,Jr.,Once More,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Wisconsin Law Review,2000,pp.573—595,at p.574.
[57]See James J.Hanks,Jr.,Evaluating Recent State Legislation on Director and Officer Liability Limitation and Indemnification,The Business Lawyer,Vol.43,1988,pp.1207—1255.
[58]See John C.Coffee,Jr.,The Regul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Litigation:Balancing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n the Large Class Ac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54,pp.877—938.
[59]See supra note 27,pp.336—337.
[60]See W.V.H.Rogers,Winfield & Jolowicz on Torts,Fifteenth Edition,Sweet & Maxwell,1998,pp.837—838.
[61]See R.A.Percy and C.T.Walton,Charlesworth & Percy on Negligence,0p.Cit.,p.125.
[62]See V.Finch,Company Director:Who Cares about Skill and Care?,Modern Law Review,Vol.55,1992,p.179.
[63]See Leon Green,Foreseeability in Negligence Law,Columbia Law Review,Vol.61,1961,pp.1401—1424,at 1420.
[64]See Paul L.Davies,Gower and Davies’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7th edition,Sweet & Maxwell,2003,p.432.
[65]See Joanna Bird and Jennifer Hill,Regulatory Rooms in Australian Corporate Law,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51999,pp.555—606,at p.562.
[66](马来西亚)罗修章、王鸣峰:《公司法:权力与责任》,杨飞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页。
[67]R.A.Riley,The Company Director’s Duty of Care and Skill:The Case for an Onerous but Subjective Standard,Modern Law Review,Vol.62,1999,pp.697—724,at p.699.
[68]Re RJR Nabisco,Inc.Shareholders Litigation,Del.Ch.Jan.31,1989,p.91.
[69]See Melvin A.Eisenberg,The Duty of Care of Corporate Directors and Officer,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aw Review,Vol.51,1990,pp.945—972,at pp.961—962.
[70]参见邓峰:《作为社团的法人:重构公司理论的一个框架》,《中外法学》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