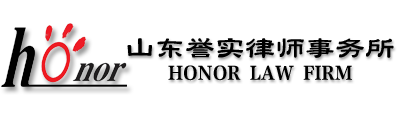杭州飙车案和成都孙伟铭交通犯罪被判死刑案引起全民对交通安全的高度关注:专家激动,网民骚动,立场不同的律师纷纷上书,专家的意见莫衷一是。从舆论效果角度看,这些并非悲悯之戏或闹腾喜剧,而是理性正剧,中国正在进入交通危险的大时代。
2005年日本交通死亡的人数是6871人;同年,我国交通死亡人数是98738人,比上年减少8339人,这个数字竟然还大于日本的年死亡数字。据保守统计,彼时中国汽车保有量为2400多万辆,而日本汽车保有量是7000多万辆。2005年至2009年,每年日本都推出“全国交通安全运动实施纲要”,警方和民间的多样措施令人过目不忘,这一运动最突出之处是随《道路交通法》的频繁修改而飙进。2007年日本重点加大了对酒后开车的处罚,其基本修改是:对酒醉后开车与酒后开车加大了刑罚力度(如酒醉后开车,处5年以下徒刑或者100万日元以下罚款);新增对提供车辆者与提供酒者或者同乘者的惩罚,牵连定罪,刑期二到五年不等。在日本,严重交通犯罪趋于重刑化。
这一现象绝不是孤立的,近年香港《道路交通条例》的重刑化趋势也非常明显:在1997年,交通罪行(1)任何人在道路上鲁莽驾驶汽车,引致他人死亡,即属犯罪———(a)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25000及监禁5年;及(b)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12500及监禁2年。在2008年,交通罪行(1)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引致他人死亡,即属犯罪———(a)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第5级罚款及监禁10年;(b)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第4级罚款及监禁2年。
但是,对交通犯罪重罚问题仅用刑法教科书进行解释,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某些刑法学者也几乎忽略了当前问题的主要论证不在刑法内,而在刑法之外。对交通犯罪问题的讨论当然不是刑法学者的专利,时下我国几乎所有论者都大胆地凭着直觉进行争论,偏重价值(安全或人道宽宥),而互相辩驳很难取得理性的统一或者意见让步,大家都忽略了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为此我推荐台湾吕宗学博士的研究结果(至少在解决争论时有重大启发)。吕博士发现:“以台湾为单位的分析结果显示所得与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之关系的确在经济发展初期呈现显著正相关,随着所得增加正相关减弱,当人均生产毛额超过6223美元(1988年)后,两者关系变成负相关,但是大于13413美元(1997年)后负相关消失。以台湾县市为单位的分析结果……当高发展地区持续出现负相关的年代,低发展地区还是持续正相关。”
而在2008年,中国人均GDP刚突破3000美元。在吕博士的客观规律之假说上(有待大陆学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我认为一切争论都应当有合理的解释:
第一,交通犯罪的重罚体现了更深刻的人道主义,即更多人的生命利益优于少数恶习犯罪者。飙车,应当定义为“违法十受罚无畏十足够的金钱眩晕感”;醉酒驾车,应当定义为“恶习十良知埋污十极端的自私感”。人性都是一样的,日本国民、香港同胞难道比大陆人更懂人道吗?就刑法功利而言,在不必要的恶习(意味着众多无辜生命的消失)与严厉的重罚之间进行选择,这对于受罚者谈不上过于苛刻,苛刻的东西是置“飙”、“醉”的社会恶习属性不顾的单面思考方式———假(伪)人道偏执症。
第二,交通危险中的牵连定罪,严格地讲并非中国古法之连坐滥用,特定社会背景(交通大危险时代)容许危险即是制造危险。容许的犯罪心理(针对整个社会,而非某具体人)是对其特定社会义务的背叛,因此连带惩罚既符合文化社会学(恶习圈制裁),也符合社会心理学(亚文化圈治理)。
第三,聪明的人道主义法学应当研究:交通事故及犯罪与经济文化之因果律,学习日本的全民交通安全运动,学习以日本、香港为代表的普遍治理方式:飙车、醉酒驾车致重大祸难应当重罚……统一的司法解释应当消除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竞合,“危险故意”的推定是价值上的武断推定(注意,学术上为什么不用“推理”表述“推定”呢?),即一种明白无误的价值选择,无需个案证明。
当然,惩罚是全民运动的很小(但必要)的一部分,真正的交通安全在于提高公民的交通安全能力(不仅仅是意识),譬如,我看过的一部纪录片:香港几十年前推行学生过街督导队(学生督导员过街示意牌的法律效率等同于交警的手势),在这一制度下,香港学生没有一人因过街而致交通事故死亡。可是,每当我提这个问题,我就在等待反驳:我们的家长敢于把安全交给自身还是孩子的过街督导员吗?人们会惊恐地说,连交警都如此如此———这就是文化,这也是全面安全运动要革除的深层法治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