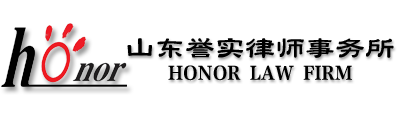【学科分类】司法
【写作年份】2009年
【正文】
在当下中国刑事诉讼研究中,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已成为观照域外法治国家诉讼模式的基本范畴;“贴标签式”认定大陆法系的刑事诉讼模式属于职权主义,英美法传统的国家则是当事人主义,似乎也成了学界的固化认识,甚至还作为一种“正确知识”被传播开来。 [1]正是基于此种前设性认知,在判别中国刑事诉讼基本模式上,人们往往认定中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形态也是职权主义,总体上与欧陆近似。 [2]进一步,在刑事司法改革的浪潮兴起之后,当事人主义或者是吸收当事人主义模式的某些要素,成为了改革的主流意见。 [3]
姑且不论这种论断是否生搬硬套,就是在基本的层面上,我们似乎对这两个概念尤其是职权主义的内涵缺乏应有认知,很多时候可能是在“想当然”使用,对于其“能指”与“所指”并不明了。由此带来的结果,除了可能会犯潜在的知识性错误之外,还会导致学术研究、交流的障碍;如果考虑到学界对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革方向所形成的认识对决策层的影响,这甚至会阻碍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真正地朝合理化方向的延展。因此,我们有必要展开关于“职权主义”的“知识考古”工作,梳理其在中国刑事诉讼研究语境中的来龙去脉,清理其在域外语境中的源流,探析“词”与“物”的复杂互动,为学术研究提供准确的理论原点。倘若笔者的这一研究取向能够激发更多同仁也致力于反思诸多往往为我们不假思索使用的概念,检讨大写般真理似的原则与理论的兴趣,则更为笔者所乐见。
一、中国语境中的“职权主义”
在传统中华法系的话语库中,“职权主义”始终未见踪影,它是否也是“舶来品”呢?它是如何出现在中国的刑事诉讼之中,又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为何它在当代中国刑事诉讼的研究与立法中有如此影响?这些隐秘在概念“深闺”中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拨开迷雾,还其真实的面相。笔者以为,在很大程度上,“职权主义”是一个中国化或东方化的概念,是东方对西方制度和理论的理解和想象,它始于清末民初的近代中国;这种理解和想象随着东西交流及中国国情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并且深刻影响了中国刑事诉讼的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对此,笔者拟通过考查相关的中文文献与话语,着力回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在“职权主义”概念使用上的历史流变来阐明前述主张。
(一)1906-1949:话语之形成与初步发展
话语的兴起,往往与物的出现与变化相关联。职权主义话语之形成,与清末“改制”及修律运动密不可分。1906年,沈家本主持制定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诉讼法典,即《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1910年,在日本冈田朝太郎博士的参与下,以日本1890年《刑事诉讼法》为蓝本,修订编成《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尽管这两部法律草案均未提及“职权主义”,但后世的一些理解都暗含在了其中。沈家本于1911年1月24日就编成《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奏呈朝廷时,在阐述修律的大旨中提到:“七曰干涉主义。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处分权,审判官不得干涉。至刑事诉松,当事人无处分权。审判官因断定其罪之有无,应干涉调查一切必要事宜,而不为当事人之辩论所拘束。” [4]笔者以为,沈氏的所谓“干涉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理解成法官的职权调查,这实际上含有今天所谓法官职权主义的意思。 [5]同时,沈家本就编成《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奏呈朝廷时还提到:“一曰诉讼用告劾程式。查诉讼程式,有纠问告劾之别。纠问式者,以审判官为诉讼主体,凡案件不必待人告诉,即由审判官亲自诉追,亲自审判,所谓不告亦理是也。告劾式者,以当事人为诉讼主体,凡诉追由当事人行之,所谓不告不理也。在昔各国多用纠问式,今则概用告劾式,使审判官超然屹立于原告被告之外,权皆两至以听,其成法最为得情之平。” [6]这似乎表明,在沈家本的理解中,纠问与弹劾之分是构建近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首要所在,而刑事诉讼中的法官职权调查则是弹劾式诉讼的重要制度构造,并不等同于纠问式。
继之急促的修律,关于刑事诉讼的研究也逐渐展开。这首先是译介外国刑事诉讼法与研究著作。由于修律大臣沈家本等人对日本的政治法律制度兴趣浓厚,日本的文献自然得到了较多的关注,如《日本刑事诉讼法》、《日本改正刑事诉讼法》、《日本刑事诉讼法论》等都被法律修订馆先后翻译;日本学界其他的研究文献,如古野格的《刑事诉讼法》、松室致的《刑事诉讼论》、石光郎的《日本刑事诉讼法理》也被译介至中国。(7〕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日文文献已提及职权主义。很可能中国学者藉此首次接触这一概念,当时的论者们对职权主义的认识也可能形成于此。事实上,中文“职权主义”一词,即系直接引入日文汉字“職権主義”而成。至于中国论者将之作为“大词”来关注,据笔者所考,较早见于1919年左德敏所著的《诉讼法上诸主义》(不排除更早的可能),这可能也是中国学者较早从理论上来讨论职权主义的著述。左氏将“职权主义”(Offizialmaximeod In-quisitionsmaxime)与“辩论主义”(Vwehan dlungsm axime)对应,等同于干涉主义,即法院的审理对象“不拘束于当事人之声明或陈述”,这似乎是为了与“当事人进行主义”(Partei-betriebod. Selbstbetrieb)对应。左氏另使用“职权进行主义”( Offizia lbetrieb)一词,以表法院主导诉讼进程之意。 [8]与左氏类似,夏勤在1923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要论》中使用了“职权主义”、“职权进行诉讼主义”与“处分主义”、“当事人进行诉讼主义”四个对应的概念来区别法院对诉讼对象、诉讼进程的控制与否。 [9]朱采真于1929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新论》也用“职权进行主义”一词,表示“国家可依职权推进诉讼,而不必待当事人之声请”。 [10]
徐朝阳在1933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通义》、陈瑾昆于次年出版的《刑事诉讼通义》都阐释了“职权主义”。两书均将其与“不变更主义”等同,而与“处分主义”对立,都认为“职权主义”之要义在于法院对诉讼标的和诉讼关系的主导权,并排除当事人进行变更、撤回或和解 [11]魏冀征1936年所著的《我国诉讼法主义之研究》亦持类似观点。 [12]这些观点的提出,表明当时的学界对职权主义的认识已有所深化,并开始尝试突破左氏早年的论述框架。1938年,国立武汉大学编写的《刑事诉讼法讲义》首先将诉讼标的和诉讼推进一并囊括到“职权主义”概念中,摒弃了以往在“职权主义”及“职权推进主义”之间的微妙区分。该书认为,所谓职权主义,既指法院可依职权对诉讼标的进行处分,也指法院可自行进行证据调查、变更期日、终止程序等诉讼活动,而不为当事人之意思所拘束。 [13]不过,郭卫在1946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论》中,又重提“职权进行主义”,但却仅将之定义为法院对诉讼标的的主导权,而未论及诉讼推进机制。 [14]
不难发现,职权主义的话语在这一时期逐渐流行起来,并渐显重要。它既是界定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一项应然准则,也指涉欲借鉴的外国刑事诉讼的重要方面。这与民国继续实行清末制定的《刑事诉讼律》(草案)有关—它会刺激研究者们从理论上去探求沈家本在编修刑事诉讼法时所述及的要旨。不过,我们也看到其语义的多样性。这一方面与制度建设的不确定性相关:从清末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一直努力从传统中华法系转向近代西方大陆模式,虽有所成就但未整体成型,这致使外来概念与中土之物之间存在似对非对的微妙关系。另一方面也与早期学者对域外对象把握与了解不足相关—其时学人多系“二道贩子”,往往依靠日本教授的传授,少有直接凭据欧陆一手资料或亲临欧陆的深研,由此使得话语表述的主体性与所指涉之词出现了模糊性。这表现为,早期学者多将其与“处分主义”对应,特指法院对诉讼标的的主导权,而另以“职权进行主义”(对应“当事人进行主义”)指涉法院的诉讼推进与调查职能;而在后期,既有学者将两概念合二为一,也有学者将两者颠倒使用。从上述辨识来看,此一时期的职权主义尚不具有“关键词”的地位,学者们也没有将其上升到诉讼体制、诉讼模式的高度,它只是用于审判阶段的,与言词审理、直接审理、公开审理等具体诉讼制度并列技术性概念而已。
(二)1949-1979:话语的历史性断裂与潜隐
新中国成立后,整个法律体系的意识形态表达与具体制度建构均与以往截然不同。在刑事诉讼的研究中,清末以来建立的诉讼法学理论及研究方法已基本被抛弃,意识形态(阶级)分析取代法学的技术分析,以经典的社会制度类型来区分诉讼制度类型成为惟一标准。因此,“职权主义”概念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并因其强调国家追诉而被指责为背离“社会主义群众路线” [15]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背景中,职权主义成了论证社会主义刑事诉讼制度优越性而必须加以严肃批判的对象,即使是在纯粹技术意义上使用“职权主义”也变成了“政治不正确”的话柄。于是,职权主义在此一时期终成学术禁忌,清末以来的职权主义话语出现在了历史性的断裂,但作为曾经存在的学术理论,它却潜隐在了人们的学术记忆之中。
与此同时,在废除国民党旧法的基础上,新中国大力引进苏联的法律制度和理论。到“文革”前,刑事诉讼理论全面苏联化,其中包括全面接受了比“职权主义”更加强调国家权力积极性的苏式“职权原则”理论。该理论认为,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是国家机关的“公法义务”,而不仅仅是其职权,无须顾及其他个人或团体的意愿 [16]这种威权式的诉讼理论,对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20世纪50-70年代刑事司法实践呈现强烈的“一体化”色彩,国家权力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十分活跃。在这种背景下,再来讨论法官是否应该发挥职权作用,以及应当如何发挥,并无多大现实意义,“职权主义”话语最终被淹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对苏式“职权原则”理论的接受以及在此之下形成的刑事诉讼制度,也为后来职权主义话语的复活埋下了伏笔。因为后来职权主义重新进入学术讨论视野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反思此时期所形成的诉讼理念与制度。
(三)1980年代:话语之复苏
在这一年代,中国刑事诉讼研究的范式出现了初步转换,即1950年代以降的阶级分析与意识形态化的研究范式淡化,侧重于刑事诉讼本身的技术规范分析出现在了一些研究之中。因此,职权主义的话语也随之复苏。
当时的学者们开始介绍西方刑事诉讼模式的具体特征,关注两大法系刑事诉讼的差异。以当时的北京政法学院与西南政法学院为代表的一些教学与科研机构编译了一批域外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知识,使得其时的学人们初窥了两大法系的刑事诉讼制度。在这一译介的过程中,学者们注意到,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概念已为域外学者特别是英美学者用以意指两大法系的审判制度 [17]由此,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概念获得了重要性,甚至开始为中国学者用以概括两大法系刑事诉讼的整体架构。张子培主编的《刑事诉讼法教程》一书就分别用“法官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概指欧陆和英美的刑事审判制度,并指出欧陆法官在法庭调查中占中心地位,须主动讯问证人,查明案件事实 [18]但作者又使用“职权主义”一词指代“国家追诉主义”(与私诉对应),并用“侦查辩论式诉讼”、“混合式诉讼”概括近代欧陆刑事诉讼整体模式,意指其“侦查是秘密的,审判则是公开的”。 [19]与张氏教材的概念使用相比,汪纲翔则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职权主义”概念。他认为“职权主义”不仅包括传统的“纠问式”诉讼,也包括近代以来形成于欧陆的“混合式”诉讼模式。 [20]换言之,他认为“职权主义”是“纠问式”和“混合式”上一层次的概念。
与此同时,裴苍龄则将苏式概念“职权原则”和“职权主义”统一起来,认为两者本质相同,但“职权原则”是苏联检察制度发展起来之后对“职权主义”的新提法 [21]到了80年代末,学界的理解进一步深入,开始从整体的诉讼结构来分析“职权主义”。比如,陈光中主编的《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认为,大陆法系国家所实行的刑事诉讼程序结构形式是职权主义,其特点在于注重发挥侦察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作用,特别是法官在审判中的主动指挥作用,而不是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的积极性 [22]严端主编的《刑事诉讼法教程》也从公诉机制与审判机制的角度将大陆法系刑事诉讼程序特征概括为:大多数案件由检察官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审判长不是消极仲裁者,可依职权主动调查证据,因而称其为“职权主义诉讼程序”。 [23]
尽管如此,但不能忽视的是,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一个明显表征是,强调刑事诉讼法阶级本质的苏联理论仍充斥于几乎整个80年代的刑事诉讼法教科书中。比如,1982年中央政法干校编写的教材在论及“资产阶级国家的刑事诉讼法”时,尽管承认有“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之分,但未及详加区别,便用大量篇幅来论证两者“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24]与之类似,1982年版的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1989年版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均将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与封建制度、奴隶制度下的诉讼模式并列,归于“剥削阶级国家刑事诉讼法概述”一章 [25]就此来说,此一时期学界对职权主义的认识,还是囿于意识形态的限制,似乎没有接续到新中国以前的学术传统。
由上可见,1980年代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尽管没有完全摆脱1950年代以来的阶级分析方法,但由于意识形态氛围日渐宽松,学者们开始从知识层面关注西方的刑事诉讼制度,对西方刑事诉讼模式的介绍与研究逐渐增多,两大法系的制度与理论渐渐重传域内,认知不断深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职权主义”的话语开始复苏,重新成了学者们研究与讨论的重要主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有学者用其来概指大陆法系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形态。
(四)1990年代以来:话语之勃兴
这是职权主义成为关键词的时代。由于苏联影响的进一步淡化,并借助日益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尤其是与英美学界的频繁对话,纯知识形态的刑事诉讼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逐步加强,直至成为主流。为英美学界所惯用的“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二元分析模式逐渐被中国学者所普遍使用,分别概指西方乃至世界刑事诉讼的两大模式, [26]并出现诉讼构造论、模式论等影响至今的比较法研究进路。由此,职权主义话语开始流行于中国刑事诉讼的研究之中。整体而言,在这一时期,“职权主义”在消解意识形态色彩的同时, [27]逐步由技术概念发展成内涵价值判断与指涉大陆法系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性概念,并进而成为理解与反观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参照系。但由于学者们大都基于各自对大陆法系刑事诉讼制度的理解,再加之不同的研究目的,学界并没有形成对职权主义内涵和外延的统一理解,很多时候看似繁荣的学术对话,实则只是“各说各话”。可以说,此一时期对职权主义的讨论,在固化人们对英美刑事诉讼/当事人主义与欧陆刑事诉讼/职权主义的分殊认识的同时,也带来了对职权主义认识歧见纷呈的局面。
1992年,徐友军在《比较刑事程序结构》一书中批判了将职权主义诉讼与纠问式诉讼等同的观点,进而将欧陆模式称为“职权主义的审问式诉讼”,与英美“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式诉讼”对应 [28]同一时期,李心鉴在《刑事诉讼构造论》一书中认为,尽管学界已经对“职权主义”的所指对象—当代欧洲大陆国家刑事诉讼构造—基本达成一致,但在具体特征的描述上却众说纷纭,极为混乱 [29]稍后的某些论著,如崔敏主编的《刑事诉讼法纲要》也使用“国家职权主义”来指称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但对其具体的特征没有展开论述 [30]樊崇义主编的《刑事诉讼法学》没有使用“职权主义”这一概念,而是运用“审问式”来指代欧陆刑事诉讼结构,与英美的“对抗式”对应 [31]陈瑞华在《刑事审判原理论》中也认为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属于“审问式”模式,又称职权主义,并强调其核心在于法官的职权调查及实体真实 [32]到了90年代后期,以徐静村主编的“九五规划教材”《刑事诉讼法》为代表,学界观点基本与李氏类似 [33]不过,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增多与外文资料的丰富,学界对职权主义(也包括当事人人主义)的认识更为精细。如程味秋的“两大法系刑事诉讼模式之比较”一文,在认定普通法系的刑事诉讼制度属于当事人主义,大陆法系属于职权主义的基础上,还分别比较了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在刑事诉讼各阶段的特点。 [34]笔者本人将职权主义的特点概括为对法官活动重要性、主动性的强调,以及对实体真实的积极探知。 [35]稍后,笔者进一步将职权主义归结为欧陆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并认为职权主义在价值与结构上都与当事人主义直接对立。 [36]
进入21世纪后,学界对职权主义模式特别是法官职能的研究持续展开。例如,龙宗智将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的特征概括为:(1)庭前进行实体审查;(2)法官主导诉讼的进行;(3)法官依职权主动收集、调查证据;(4)不受“辩论原则”的严格限制;(5)庭审分为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两阶段 [37]孙长永在区分法官的诉讼推进职能与证据调查职能的前提下,进一步概括了职权主义模式在法庭调查阶段的特征:(1)定罪与量刑在同一程序中进行,实行相同的证据规则;(2)以审问被告人作为证据调查的基础;(3)证据调查依循实体真实原则实施,缺乏明显的阶段性,但与法庭辩论截然分开 [38]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一些学者似乎已经超越了运用“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来指涉两大法系刑事诉讼整体模式/结构的认识,他们往往从整体上论述现代刑事诉讼的一些共同性特征与发展趋势,或是使用一些内涵与外延更为丰富、涵设范围更广的概念来描述域外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 [39]
职权主义话语在此阶段的勃兴,实际上是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是上述提及的外在视角,即辨析大陆法系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二是内在视角,即讨论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类型。在对两大法系刑事诉讼制度进行比较观察的同时,一些论者将研究视角转向了中国,开始运用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这对概念来讨论中国刑事诉讼的模式问题。例如,徐益初认为,中国的刑事诉讼结构既不属于超职权主义的诉讼结构,也不是纠问式的结构,与当事人主义有很大差别,比较接近于职权主义,但也有自己的特点。 [40]李心鉴也认为,中国的刑事诉讼构造虽然具有某些当事人主义的因素,但就构造的主要方面而言,是属于职权主义类型。 [41]笔者在1994年也持类似的看法 [42]还有论者从模式转换的角度认为,中国刑事诉讼模式应从职权主义转向当事人主义。 [43]侧重于从审判模式的角度来讨论中国庭审模式的论述亦较多。论者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的庭审基本上属于职权主义范畴,鉴于中国庭审制度存在的问题,未来应该借鉴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的一些做法 [44]后来关于中国刑事审判模式改革的“混合式”主流意见就滥觞于此。在刑事司法改革的话语兴起之后,以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刑事审判制度为对象的职权主义话语更是喧嚣一时,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不一而足。
综上,随着百年来制度建设的发展与转换,并基于对“词”与“物”复杂互动关系的把握,在国际交流与对话的大背景下,在想象与认知外来之物的过程中,在勾勒中国图景与生产中国理论的进程中,中国学界关于“职权主义”及对应“当事人主义”的话语呈现出了明显的知识性流变:从最初界定刑事诉讼的具体诉讼原则,到区别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标签,再到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尔后归结到对欧陆/英美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概括,及至界定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最终,“职权主义”完成了从籍籍无名的“小词”到举足轻重的“大词”的转变。在笔者看来,“职权主义”话语的“出现一淹没一复苏一勃兴”发展过程,实际上在某种程度凸显了整个中国刑事诉讼知识体系在20世纪的发展与转型:大陆法系的知识体系—苏联法系的意识形态—英美法系的理论谱系。可以说,正是因为该话语在不同知识谱系中大不一样的意义,使得话语的作用力在不同年代、不同知识支配背景下,也迥然不同。当然,学界在长期的对话和讨论中对职权主义的理解虽不免分歧和模糊,但已达致某些共识,词与物的契合性明显增强。二、域外语境中的“职权主义”
(一)日文语系中的职权主义
近代化伊始,日本法学家与日本刑事诉讼制度便给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制度建构与研究以极大影响,中文“职权主义”一词,也系直接引入日文汉字“職権主義”而成。因此,有必要考察职权主义在日文中的来龙去脉,但因资料来源及语言能力所限,在此只能略析一
一般而言,日语中的“職権主羲”可能译自德国刑事诉讼中调查原则(Untersuchungs-grundsatz)。从笔者所掌握的日文文献来看,板仓松太郎可能是日本学者中较早详细论及职权主义的学者。他在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玄义》一书中专章论述了刑事诉讼的各种主义,他将纠问主义、弹劾主义并列,职权诉追主义、个人诉追主义并列,当事人进行主义、职权进行主义并列,认为当时日本实行弹劾主义、职权诉追主义、职权进行主义。 [45]此后,平沼骐一郎在大正十二年(1923年)出版的《新刑事诉讼法要论》中提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观念包括实行职权诉追制与职权审理制,职权诉追制意指由公诉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职权审理制意指法官基于实体真实发现主义,不若民事诉讼般实行处分权原则,而对事实与证据进行不全然受当事人拘束的调查 [46]稍后,牧野英一在1940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一书中则未作此类区分,但也将“职权主义”视作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之一,并将之与实体真实主义紧密联系,即法官得不受当事人的限制,依职权调查证据 [47]由此看来,“职权主义”同样是二战前日本刑事诉讼研究中的重要话语,由于其被列入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甚至可说比其在继受国—中国的地位更显凸出。不过,它只是与弹劾主义、便宜主义、直接口头辩论主义、公开主义并列的一个刑诉理念而已, [48]难以用之界定整个日本刑事诉讼制度,而更适宜界定刑事审判中的法官作用方式。事实上,从牧野英一认为刑事诉讼进化史是从弹劾主义一纠问主义一当事者主义演进的论述也可以看出,牧野教授似乎并不认为职权主义是刑事诉讼发展历程中的某一独立阶段,也没有将之与当事人主义并列的意涵 [49]据此,结合受日本学界影响较大的中国清末与民国时期中国研究者对职权主义的一些用法,可以大致推及的是,职权主义话语尽管在二战前的日本学界较为流行,但并没有成为日本学界从整体上理解刑事诉讼制度的关键词,日本学者也没有将其作为界定欧陆刑事诉讼制度模式的概念性工具。换言之,二战前日本学界对职权主义的理解似乎接近大陆法系语境中,尤其是德国语境中的“调查原则”的本意。毫无疑问,这与其时的日本深受大陆法系的知识之影响有关,特别是法国、德国的影响。
二战后,由于日本刑事诉讼制度的急剧转型与英美法系知识的流行,日本学界对职权主义的讨论有了一定的变化:研究的视角与研究的知识论基础以及具体的看法,均与二战前有所不同。整体而论,其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是当事人主义成为当代日本学界研究职权主义的重要出发点。换言之,不少研究是一种“当事人主义视角”的职权主义研究。受日本刑事诉讼英美化的影响,一些学者基于inquisitorial/adversary的二元模式,从当事人主义的角度来认知职权主义。比如,滝川幸辰教授在1960年代对职权主义必要性是如此阐释的:由于“发现实体真实”是“刑事诉讼法的根本使命”,而当事人主义不一定能实现该目标,当其“背离这种期待,或者将要背离这种期待时,为了实体的真实主义当然要允许法院的干涉” [50]也就是说,职权主义—更准确地说,是职权审理主义,本质上是作为当事人主义的补充而得到学界和实务界认可;职权主义的必要性,仅在于发现实体真实方面的比较优势。田口守一教授对《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94条的理解其实也是此种思路。田口教授认为,该条文是对法院诉讼指挥权的规定,即普遍称的“职权进行主义”,作为源自司法权的法院固有权限,诉讼指挥权是为了当事人诉讼追行顺利而行使的职权,并不直接关系诉讼的实体问题,因此并非与当事人主义对立的职权主义,尽管它是日本刑事诉讼“职权主义”特征表现之一 [51]
其二是将职权主义视为“纠问式”和“弹劾式”等模式论、构造论的下位概念,而非同位概念。具体地说,相当部分学者延续战前的研究,不将职权主义视为对欧陆刑事诉讼模式的整体性概括,而认为是对刑事诉讼局部特征的描述。比如,高田卓尔教授就认为:“纠问式必然与职权主义相结合,但弹劾式既可采纳职权主义也可采纳当事人主义。根据在程序的哪一部分承认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可以对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进行进一步区分。第一,就诉讼对象这一部分而言,如果交由当事人处分就叫辩论主义或(当事人)处分主义,如果交由法院全面支配就叫职权(审理)主义。第二,就证据的收集和调查这一部分而言,如果交由当事人进行就叫辩论主义,如果交由法院依职权进行就叫职权(探知)主义。” [52]可见,高田教授所称的“职权主义”,实际上就是中文语境下的“职权主义特征”或“职权主义色彩”,而非“职权主义模式”。团藤重光教授就二战后日本刑事诉讼法的变化指出,旧法(日本战前刑事诉讼法)当时的当事人主义的意义在于补充、控制法院的职权,而在现行法中,毋宁说职权主义被视为补充性的原则。“不过,实现刑罚权本来是国家关心的问题,当然由作为国家机关的检察官充当原告官,从国家的立场出发完成公诉职能。但是,作为审判主体的法院也是国家机关,当然也必须积极关心刑罚权的实现,因此,就刑事审判而言,必须承认职权主义是其本质性的东西。新法虽然强调当事人主义,但在其背后总是潜藏着职权主义,并在必要时就浮出表面。只根据表面的考察,认为当事人主义已经取代了职权主义的观点,应当说是没有看到刑事审判的本质。就此意义而言,可以说刑事诉讼是把职权主义的内容装人当事人主义的形式当中。” [53]不难发现,团藤教授所使用的职权主义概念仅局限于审判程序,与审判程序中诉讼主导权属于法院还是当事人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松尾浩也教授在1979年出版的《日本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提及职权主义的概念,在论及刑事诉讼法的类型时,直接从刑事诉讼目的共性与差异的角度使用了大陆法系类型和英美法系类型 [54]
其三是注意研究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调和。日本二战前后立法模式的差异与二战后实务与立法的距离,促使日本学者特别关注两大诉讼模式的协调问题。井户田侃便关注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构造的嫁接问题,并发现其困难性。 [55]田宫裕也发现司法实务中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因素并存且都“片面化”。 [56]而平野龙一教授在评述日本二战后刑事诉讼法的变革时也指出,“新法积极构建与旧法不同的结构,以当事人主义为其基本因素,在此基础上施以适当的职权主义修正。……新法把检察官从法院中分离出来,使之与被告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在强化被告人地位的当事人平等主义这一点上相当彻底,但在把诉讼的主导权赋予当事人而表示法院,即所谓的辩论主义这一点上却未必是彻底的。” [57]
显然,与中国类似,在明治以后大规模的借鉴、引进外来制度与法律知识的背景下,职权主义的话语似乎在日本也有一个无中生有、逐渐发展过程。一方面,从战前重要但不突出的位置到战后的“热词”,话语指涉度显现一种上升态势。这大概与日本二战前后经历了大陆法系到英美法系的制度和知识转型相关,由此使得大陆法系语境下并不特别重要的职权主义在借鉴英美法系的背景下成为了重要的热词:不仅有学者以此来界定大陆法系刑事诉讼模式,还学者以此作为关照二战前日本刑事诉讼整体特征的工具 [58]但另一方面,制度转型的不彻底性与知识谱系的多样性,使得日本刑事诉讼研究出现两种知识传统与研究范式共生的格局,由此导致日本学界在使用职权主义时颇显犹豫:既未如二战前欧陆话语构架下那样用于有限界定制度局部,也未单纯从英美二元模式来厘清整体构架,似乎游离于二者之间,摇摆不定。这不仅表现在理论探讨上不同知识传统下多种话语的并存,也体现为多数日本学者较少用之来界定日本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模式,而更偏向确定文本上制度的对抗性或正当程序性 [59]
但更需看到的是,与中国相比,日本对外来理论与制度的把握更为精当,制度建设也先行,从而在近代化上充当了中国的老师。对照二战前中日学界关于职权主义的话语表述便可发现惊人的相似或一致,以至很容易便可判定两者的相关性。就此而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职权主义话语表述所带有的大陆式的印迹,主要来自日本的影响,尽管中国学者的认知同样有着自己的本土背景与个体的主观理解。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的刑事诉讼制度建设与理论研究长期亦步亦趋于西方国家,日本学界在二战前似乎把握了大陆法知识谱系下职权主义的真谛。但在接触与吸收了英美法系的知识之后,日本学界对职权主义的理解相反显得有些游离不定了,各种话语也是“诸神并列”,难成定见。这显示,在两种不同知识谱系的碰撞下,日本学界并没有在理论上寻求到能融合两种不同知识传统对职权主义不同理解的良径。
(二)英文语系中的职权主义
从上文对中文与日文语系下职权主义的梳理中,可以发现英美关于欧陆刑事诉讼制度的认识,对当代中国与日本学界的影响较大。那么,英美学界到底是如何认识欧陆刑事诉讼制度?这种认识在英美学界又经历了如何的变迁?英美是否也有“职权主义”或类似的话语?显然,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详勘。下面笔者将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略述如下。
一直以来,英美学界关于比较刑事诉讼研究的主流范式是“inquisitorial/adversarial”的二元模式,这是英美以自身为中心来关照他者、界定自我的基本模式。郎本指出,长期以来,英文学界一般用“inquisitorial”一词描述欧陆刑事诉讼模式 [60]尽管不能精确锁定其初用时间,但至少可以认定是在法国大革命前后 [61]至于何谓“inquisitorial system”,West’s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Law一书的界定是,在审判中代表国家利益,法官致力于发现事实的一种实践方法,并指出其首先形成于中世纪的天主教会,而在法国大革命后经过了更好的提炼 [62]还有英美学者将审前程序也纳入了界定范围。尽管具体表述不一,但包括不同时代的绝大多数英美学者对“inquisitorial system”或“ inquisitorial justice”的基本理解还是大致相同:其结构基本上类似于一项官方调查,大多数程序活动是由官员们来推进的 [63]
当然,总体而言,英美学者在关注欧陆国家在事实调查中的积极作用和绝对优势的同时,也在深入探讨现代“inquisitorial system”的特征, [64]并试图作出更深刻的阐释。如英国学者J. R. Spencer就对“inquisitorial”与“accusatorial”进行了详细的辨析。Spencer批判了将“inquisitorial”与官方追诉、书面化秘密司法、有罪推定、被告人客体化等概念等同的观点, [65]进而将“inquisitorial”模式的特点归纳如下:首先,欧陆刑事诉讼法典大多原则性规定法院有查明案件真相的义务。其次,欧陆缺乏有罪答辩制度,控辩双方也不享有界定争点范围的权利。再次,法、比、德对证人的询问主要是由主审法官进行。复次,许多程序事项由法庭而非控辩双方确定。最后,预审法官在侦查中比较积极。 [66]另一名英国教授Richard Vogler则将“inquisitoriality”的整体特征表述为:权威主义,程序的官僚化、持续性,以压力获取被告合作,理性演绎与调查 [67]还有学者如UCLA的Maximo Langer还提出,借鉴韦伯的理想类型,可将inquisitorial与adversarial概念化,作为理想类型来分析大陆和英美的刑事诉讼制度。 [68]
显然,若从词源与内容上考察,英语中并没有专门术语表示汉语中“职权主义”的意思。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不少英美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陆刑事诉讼制度似乎只是“同一树干上的不同枝条”,没有必要区分传统纠问式和现代职权主义。 [69]由此来看,“inquisitorial”一词在字面上似乎翻译成纠问或审问更忠实于语意。当然,根据语境的不同,翻译成传统的“纠问式”或现代的“职权主义”也不无道理。因此,当下所谓的“职权主义”,与其说是英语世界的概念,毋宁说是东方世界尤其中国对特定语境下“inquisitori-al”一词的解读。
需要指出,英文学界对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理解与欧陆传统上的纠问式诉讼有关。早在12世纪,欧陆因区分有无原告发动诉讼程序便已使用对抗与纠问的话语,尽管这与今天人们包括英美学界对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理解颇不相同 [70]正是基于对传统欧陆刑事诉讼制度以及欧陆学者见解的认知与批评,英语学界最初针对法国大革命前的欧陆刑事诉讼模式形成了inquisitorial/accusatory或adversary的二分法,并在“accusa-torial”的对立面定义“inquisitorial”。尽管如此,当古典的“accusatorial”自近代以来在英美法系发展为指涉现代的“adversary ”概念时,英美学界关于“inquisitorial”的研究却未能发展出更贴切的对应概念,以意指早已大踏步前行的欧陆刑事诉讼制度。虽然早在法国大革命后,基于制度变革的现实,欧陆学者便用“mixed system”来界定欧洲刑事诉讼制度 [71]于是,问题便出现了。
其一,绝大多数英美学者居然不考虑时代差别,始终笼统地以“inquisitorial”泛指古今的欧陆刑事诉讼。个中原因,也许正如达玛什卡所言,后革命时代的欧陆司法改革,书本上的宣言上比实际的操作更为成功 [72]以至于在强调两造平等对抗、法官消极裁判的英美学者眼中,即便在当代欧陆国家,颇为流行的半秘密侦查、法官主动等因素也可能带有中世纪的纠问色彩。所以,如果完全以现代制度层面“adversary”为标准来观照欧陆刑事诉讼的实践,在最原初的意义上使用“inquisitorial”来指代欧陆模式,似乎很难说有什么不妥。达玛什卡便持有这一看法。他指出,后革命时代的欧陆刑事诉讼制度,从英美观察者的角度看,完全吻合于非抗辩式或政策实施型的司法模式 [73]但是,由于“inquisitorial”的中世纪“出身”,总让人联想起恐怖的宗教裁判、法定证据制度、刑讯逼供、控审不分、有罪推定、秘密司法等。也就是说,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inquisitorial”失去中立的意味,而暗含有弱化人权保障、强调国家专制的价值判断 [74]就此来说,若不加区别地使用该概念,将容易使人们以为当代欧陆刑事诉讼制度仍然盛行专制主义,看不到200年来的巨大变化。实际上,经过对中世纪司法的反思和改造,当代欧陆各国人权保障状况并不低于英美国家。因此,再笼统地以带有贬义的“inquisitorial”一词指涉现代欧陆刑事诉讼,似有不当之嫌。德国学者赫尔曼就此曾指出:“对那些不十分熟悉德国刑事程序的外国人来说,“inquisitorial”一词可能会(事实上已经)造成误解。它可能在暗示人们德国似乎还在实行那种秘密进行的法庭程序:法官拥有不受限制的调查权,被告人没有律师协助,也不受无罪推定原则等的保护。但实际上,在以前的时代,这种类型的程序确在德国和其他欧陆国家存在过。但在19世纪上半叶,原有的古老纠问式程序已被一种革新的纠问式程序( reformed inquisitorial system)所代替,后一种程序建立在自由主义、人权以及启蒙哲学之上。” [75]正是看到欧陆国家近代尤其二战后在人权保障上的长足进步,二战以来,渐有英美学者呼吁重读“inquisitorial system”,甚至还主张学习与借鉴欧陆刑事诉讼制度 [76]
其二,英美刑事诉讼传统上以审判为中心,审前程序曾长期不受重视。而大陆法系则长期倚重审前程序,即使法国大革命后的混合制也是一种笔者称之为“两阶段式”的司法模式。因此,以审判为中心的两分法式的研究与界定并不适用于关照欧陆的制度与实践。更何况审判程序还是欧陆受英美的accusatory system影响最大的部分,是其最不“ inquisi-torial”,而相对“accusatorial”的部分 [77]
也许正是看到症结所在,达马什卡教授抛弃了以“inquisitorial”指涉职权主义的传统,转而使用“non-adversarial”(非对抗式)一词。他指出,传统的“adversarial”/“ inquisitori-al”二分法严格说来多有偏颇:前者一定程度上是对英美模式的理想化,后者又对欧陆模式的消极因素有所夸大。实际上,曾经被英美学者反复强调的所谓欧陆模式的缺点,如有罪推定、强制获取口供、任意性搜查等,尽管早已埋进历史的故纸堆,却仍然被英美学者津津乐道。达马什卡把这种“英美优越论”视为英美学者“难以抗拒的诱惑” [78]鉴于20世纪前期确立的历史三分法(弹劾式、纠问式和对抗式)在20世纪后半期已不再完全适用,特别是“inquisitorial”的使用呈现模糊和扭曲,达马什卡建议另以“non-adversarial”(非对抗式)指涉法国大革命以后确立起来的职权主义诉讼制度。他将非对抗式诉讼的本质概括为由官方主导的查明犯罪并明确刑罚的三方调查程序,而非解决纠纷的对抗模式 [79]当然,达氏更大的贡献,还在于跳出了传统分类法的窠臼,独创了“科层/协作”及“政策实施/纠纷解决”的分析框架 [80]但正如他本人所说,这种分类总体上是“理想型”的,他也无意将其与英美/欧陆模式直接对应。限于本文的主旨,此处也不再着笔墨。
因此,英美当下不少研究分析已基本消解了“inquisitorial”,一词的中世纪色彩。不过,虽然英美关注比较法的著名学者大多持有类似相对肯定的思路,但目光向内的多数英美学者依然抱有“本土的自信”,否定欧陆仍为主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inquisitorial system”的表述在英美学界乃至世界学界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它已成为英美学界对欧陆刑事诉讼制度根本特征的整体性界定。这是其他语系的学界包括欧陆学界所未有的。尽管欧陆也有部分学者采用英美的认识范式来评判欧陆的刑事诉讼制度,但主流的见解还是视法国大革命后欧陆的刑事诉讼为“混合式”或“改革”后的刑事诉讼 [81]其二,它已成为英美学界对欧陆刑事诉讼模式的历时性评判。英美学者似乎少有关注大陆法系刑事诉讼的发展,且对其历史性变化缺乏足够的敏感。无论欧陆在200多年来有何变化,均不以为意,仍视作“同一树干上的不同枝条”。其三,“inquisitorial system”一词不仅指涉过程结构,而且往往具有否定性价值评判意味。Stephan Landsman就认为,“inquisitorial system”更关注实体真实,而非个人权利,整体上并不审查政府权力 [82]事实上,诸多英美学者均以对抗制为傲,批评大陆刑事诉讼制度。其四,它深刻影响到了其他法系学者,尤其是东方国家学界的理论认知。这主要表现在二战以后,随着美国软硬实力的膨胀,作为美国重要象征的“对抗主义”及相应理论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有着极大影响,而且对相对弱势的发达国家也颇有影响。以对抗式为取法对象,视非对抗为纠问/职权主义且予以摒弃,成为一些国家的取向。虽然,达马什卡等人看到了其中不合理之处,但其使用的“non-adversarial”(非对抗式)一词仍不免有“英美中心论”的嫌疑,具体含义也难以精当把握,更无法指涉英美之外、差异颇大的各种制度。
特别需要指出,中文学界同样在1990年代后以“职权主义”界定自身与欧陆,这与英美学术理论的强势影响有关。不过,问题在于将对物的认知与表述建立在他者的认知与表述之上,是否妥当?因为不论他者的认知还是对他者认知的认知,无疑都带有主体间性。“inquisitorial”一词固然是英美学界对欧陆刑事诉讼的理论化认知,但这种见解本身具有相对性、有限性,难说精当。同样,除去语词翻译对接的问题,中国学界将“inquisitori-al”解读为“职权主义”,当然有其理由,但也未见能全面把握其含义。尽管如此,由这种话语影响力的现象,我们是否会颇具反讽地发现,一种制度的界定往往操之在人,而非决之在己。难道不是谁掌握话语权,谁就掌握了决定权吗?
(三)法、德语系中的职权主义
如果说英美学界的论述有雾里看花,局外人品头论足意味的话,欧陆学人自身的认知便特别值得关注,特别是法国与德国学界的相关认识。
作为“现代职权主义”话语流行的制度发源地,法国人如何认为呢?在现代法语中,描述与职权主义有关的词汇主要有两个:其一是“inquisitoire”,该词的基本含义是审问制,具体指由法官“控制、管理和指挥”诉讼的制度;其二是“inquisition”,在词源上源于拉丁语 [83]该词本身是教会的用语,指教会的一种特别法院,即宗教裁判所;后来也指“专横的”、“专断的”。基本与英语中的同一词语意思一致 [84]不过,总体上,多数法国学者并未使用“inquisitoire”来描述当代法国刑事诉讼制度。在法语中,这两个词最初皆被用来指涉法国大革命以前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 [85]
法国学界认为,当代欧陆刑事诉讼制度诞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后,以1808年《重罪审理法典》颁行为标志。有意思的是,新制度一方面体现了对中世纪纠问式诉讼的强烈反思,但另一方面却是法国大革命期间从英国引进的控诉式诉讼。最终的结果采取了“折中”的手法:既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纠问制(当然抛弃了其中不人道的因素), [86]适用于审前阶段,又在庭审中保留了控诉机制 [87]然而,对这种将纠问制“嫁接”到弹劾制之上的模式,法国学界早在一百年前即有专门的术语予以概括。有学者将刑事诉讼制度的类型归纳为三种:控告式、纠问式、混合式,这三种模式在欧陆前后交替,而在法国大革命后实行混合式。 [88]学者也称之为“变革后的”刑事诉讼,甚至直接称为“折中”刑事诉讼 [89]这种模式虽几经修改,但基本结构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今天中文意义上“职权主义”的现实典型。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大革命后,inquisitoire的用法也未彻底消除。因为所谓的“混合式”(systeme mixte)是由审前的inquisitoire程序加审判的contradictoire程序组合而成, [90]但由于审前程序对犯罪控制的实用性意义,整个诉讼结构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传统的in-quisitoire色彩,因此法国学界并不完全排斥使用inquisitoire或者inquisitorial。事实上,法国自1953年以来的多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也并不忌讳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消除纠问式的残余” [91]但在这种意义使用时指的是一种延续下来的历史传统(tradition historique-meat inquisitoire)。
德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也是法国大革命后的产物,深受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的影响。与法语类似,德语中也没有与中文“职权主义”对应或相似的语词。但德语中有类似日本与中国学者所使用的“职权主义”的话语表述,其甚至可能直接构成中日相关词汇的来源。我国台湾学者林钰雄就认为,中文“职权主义”(或职权进行主义)源于德文“Un-tersuchungsgrundsatz”一词(与该词同义的表达还有“Ermittlungsgrundsatz” , “ Instruktion-sprinzip” ,“Prinzp der materienllen Wahrheit”)。 [92]在德语中,职权主义(Untersuchungsgr-undsatz)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语境中又稍有差异,在民事诉讼中对应辩论主义,在刑事诉讼中对应纠问主义(Inquisitionsprinzip),但往往又等同于国家追诉原则(Offizialprinzip)。 [93]不过,Untersuchungsgrundsatz字面意思为“调查原则”或“澄清义务”,也有德国学者称之为实质真实原则、侦查原则或者纠问原则,意指对于提交裁判的争议事实,法院可依职权调查、引入诉讼并确定其真实性,不受诉讼参与人之声请或陈述之拘束 [94]但这一实质内涵,魏根特教授却使用了“Amtsermittlungsgrundsatz”一词(国内翻译成职权原则),且将之扩大至了审前阶段—“是否指控犯罪嫌疑人的决定以及最终的判决都应建立在最接近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决策者必须在客观充分的事实基础上作出决定,而不依赖于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积极参与或是消极抵抗。” [95]显然,在德国语境中,这一项具体的诉讼制度,甚至理解成是德国的诉讼理念也并非不妥,但无论如何,它绝非是对当代德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整体概括。
实际上,如同法国学者一样,早在19世纪80-90年代德国学者已将刑事诉讼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弹劾式、纠问式和混合式,混合式制度又被称为“改良的刑事诉讼程序”, [96]具体指代拿破仑《重罪审理法典》后的法国模式,以及受其影响的欧陆其他国家(包括德国)所采取模式 [97]当然,德国学界相对较英美化,魏根特教授仍坚持审问式是德国刑事诉讼的重要传统,但他也不忘强调现代德国刑事诉讼制度多种法律因素的(包括了法国刑事诉讼制度)混合特征与19世纪的重要区别 [98]但按照达马斯卡的说法,在“混合式”和“改良式”之间,德国学者似乎更倾向于后者,因为这意味着对纠问式诉讼的改进,而非仅仅在纠问式和控告式之间的折中 [99]
由上可知,在法、德语系中均缺乏文义上直接与中文“职权主义”对应的术语。虽然欧陆学者也使用“职权原则”的概念,但这只是对欧陆刑事审判之一个重要原则的表述。欧陆学者大多习惯用“改良式”、“混合式”来指称当代欧陆刑事诉讼的整体模式,这当然比英美学者常用的“inquisitorial system”更显贴切,但与指称英美制度的“对抗式”或“当事人主义”相比,似乎略显语义模糊。无论如何,以职权主义来意指欧陆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模式并非当代欧陆普遍的自我认知,尽管欧陆一些学者有此类论述。就此而论,中日两国百年前的界定可能大致不错,问题的出现更多是与另一种知识谱系的引入相关。但当下中国学界仍以职权主义来指称欧陆的刑事诉讼制度,是否显得有些一厢情愿了?三、初步结论与反思
通过域内外语境中“职权主义”使用情况的初步梳理,可以发现:当下英美及欧陆学界均没有可与中文“职权主义”在语义上完全对应的术语。如果我们以当代欧陆刑事诉讼模式为“职权主义”的指称对象,且定位于与中世纪纠问式诉讼相区别,则可以看到:(1)英美学界对欧陆刑事诉讼存在广泛的误读,甚至长期将纠问式诉讼与当代欧陆诉讼混淆在一起。当然,以达马什卡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已经开始走出这种误区,并在类型分析上作出了开创性的尝试。需要注意的是,客观而言,中文学界往往按照自己的理解,将英语里的“inquisitorial”翻译为纠问式或职权主义,虽有牵强附会之嫌,但也不无道理。(2)欧陆学人对自身制度的认识更为全面与综合。德国和法国学界将当代欧陆模式和传统纠问式、对抗式均作了区分,并普遍使用折中性的“混合式”或“改良式”指涉前者。尽管德国刑事诉讼法上之“调查原则”很可能系中文“职权主义”的语源,但德国学界更多是在具体诉讼制度层面上使用,未提升到诉讼模式的高度。(3)日本学者长期将欧陆刑事诉讼的“调查原则”解读为“职权原则/主义”,二战后,由于英美的影响,有学者用以指涉欧陆整体制度,其发展脉络与中文学界有类似之处。该词汇虽系欧陆概念的翻译,但似乎已明显打上了东方国家对国家权力看法的烙印,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但日本对两大法系有相对长期深入的了解,使其并未普遍、简单地以之界定欧陆整体。当然,在英美谱系的刑事诉讼法知识渗入后,日本学界在职权主义认识上的多义性与摇摆性,也清晰可见。(4)中文世界的“职权主义”概念具有发展性、复杂性与独特性。一方面,它是日本、欧陆与英美三重影响下的演变之物,受到几种不同知识谱系的交叉影响。因而既抓住了“职权”这一欧陆内涵,又采用英美式的整体指涉。另一方面,它又是分析外来制度与构建、评判本土模式的双重武器。但中国学界(尤其是新中国以来)在整体上对职权主义的想象与误读,无论如何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也是必须承认的。
可见,“职权主义”一词并非国际通行之比较法学术语,而是一个东方化尤其中国化的概念。在西方语境中,我们或许能找到指涉对象近似的整体性相关术语(如“inquisito-rial”“ non-adversarial”等),但其并不完全具有中文“职权主义”的含义。我们甚至还能找到字面意思基本相同的词语(如德语之Untersuchungsgrundsatz),但其并不具有全局性的界定意义。因此,无论何种表述,若不加推敲地直接与中文“职权主义”等同,不仅于逻辑上难以通达,也难以实现有效的学术对话和交流。更何况正如本文开篇所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还在于,中文学界自身尚未对“职权主义”之外延和内涵达成充分共识。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感慨:反思一些我们不加思索而使用的语词,检讨大写般真理似的原则与理论,多少会有些发现与收获;倘若深入其中,那些惯常使用的概念与理论的坚固基石便似乎开始滑落,其坚不可摧的客观性也会受到挑战,而隐藏不显的主体性则开始表露。它们与其说是对实在之物的真实摹写/描述,不如说是主体基于自身独特背景、需要及可能自己也未意识到的有限视角,在参考外来知识谱系的情况下,针对实在之物的认知、想象和创造。不仅东方对欧陆的认知与解读如此,英美对欧陆的认识也概莫能外。理解他者也即翻译他者,其准确性始终带有主体间性。按照福柯的观点,话语生产是受到控制、挑选与分配的,知识并非连续不断的真理
[100]从本文的实例,我们似乎同样可以感受到话语表述的相对性。那么,其他的大词呢?中国刑事诉讼理论话语库中一些似乎不证自明的概念应否重新审视呢?
【注释】
[1] 最明显的表征就是时下一些影响较大的教材在论及此刑事诉讼结构/模式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采用了类似的 观点。如卞建林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2002年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 -28页;龙宗智、杨建广主编:《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第三版,上》,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6页;等等。
[2]代表性论述可参见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0-161页;徐益初:“试析我国刑事诉讼结构的特点及其完善”,《法学评论》1992年第3期;左卫民:《价值与结构:刑事程序的双重分 析》,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页,等等。
[3]相关论述可参见卞建林、李菁菁:“从我国刑事法庭设置看刑事审判构造的完善”,《法学研究》 2004年第3期;龙宗智:“试析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方向与路径”,《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1期;汪海燕:“法文化共性、相异性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转型”,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5期;等等。
[4]沈家本:《刑事诉讼律告成装册》,转引自李贵连:《沈家本年谱长编》,中国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70页。
[5]最近笔者在德国马普外国及国际刑事法律研究所看到板仓松太郎著的《刑事诉讼法玄义》(严松堂书店明治四十三年即1910年出版),其中明确将职权进行主义又称为干涉主义(参见该书第281页)。考虑到同一时期日本学者帮助起草刑事诉讼法的情况,这当可佐证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也有此意。
[6]参见前引4,第367-368页。
[7]李春雷:《中国近代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 - 33页。
[8]左德敏:“诉讼法上诸主义”,《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3期(1919年3月),转引自何勤华、李秀清主编:《民国 法学论文精萃:诉讼法律篇》,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9]夏勤:《刑事诉讼法要论》,法律评论社,民国十二年初版,二十年再版,第19-20页。他认为,“职权主义者,不问私人要求与否,国家依据刑事诉讼法及刑事诉讼之特别法,以职权开始诉讼并诉追处罚之主义也。……追诉处罚除有特别规定外,不为私人意思所左右。”
[10]朱采真:《刑事诉讼法新论》,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35-36页。他认为,职权进行主义“是法院对于诉讼的进行或终结,本于职权而为必要的行为,不必定要顾及当事人的意思以及等他前来声请”,而具体制度包括法院依职权确定管辖、调查证据、传唤证人、发还赃物等。
[11]参见徐朝阳:《刑事诉讼法通义》,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3页;陈瑾昆:《刑事诉讼通义》,北平朝阳学院出版社1934年版,第6页。需要注意的是,徐书把“处分主义”与“当事人进行主义”等同,均指当事人有权任意处分 诉讼标的。
[12]魏冀征:“我国诉讼法主义之研究”,《法学论丛》第2期(1936年2月)。
[13]国立武汉大学:《刑事诉讼法讲义》,第115-116页。
[14]郭卫:《刑事诉讼法论》,会文堂新记书局1946年发行,第8页。
[15]比如,当时最为重要的法律期刊《政法研究》中的一篇文章就认为,“职权主义”是国民党学者所称的“国家追诉主义”,它镇压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共产党人、革命人民及其他工农群众的,这种反动的“国家追诉主义”我们是坚决反对的;虽然我们国家大部分刑事案件都是由公安、检察机关侦查和人民检察院起诉和支持公诉的,但这种 活动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和支持的群众路线的基础上进行的,不是公安、检察机关孤立主义的活动;我们是采取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原则。参见张辉、李长春、张子培:“这不是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评曲夫‘略谈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诉讼地位”’,《政法研究》1958年第4期。
[16] [苏]M·A·切里佐夫:《苏维埃刑事诉讼》,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译,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117-118页。
[17]参见 [英]大卫·巴纳德:《诉讼中的刑事法庭》,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诉讼法教研室1981年编译,校内发行。
[18]张子培主编:《刑事诉讼法教程》,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页。
[19]参见前引18,张子培主编书,第2、15页。
[20]即控诉式与纠问式的混合。详细论述参见汪纲翔:“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载《政治与法律》1982年 第2期。
[21]裴苍龄:“论刑事诉讼中的职权原则”,《法律科学》1988年第1期。
[22]陈光中主编:《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5页。值得注意的是,该著作对刑事诉讼结构/模式的认识与此前不同。此书在整体考察西方刑事诉讼制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认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刑事诉讼共同遵守下述原则:一是起诉和审判职能分开,实行不告不理;二是确认公诉人、被告人都是当事人并与法院一起构成诉讼主体。进一步,该书认为,在上述两个共同原则之下,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结构模式者属于当事人主义诉讼或辩论主义诉讼,后者属于职权主义诉讼,而日本则是结合了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日本式的当事人主义”。详细论述参见该书第10-19页。
[23]参见严端主编:《刑事诉讼法教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24]参见中央政法干校刑法、刑事诉讼法教研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讲义》,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 23页。
[25]参见前引18,张子培主编书,第12-18页;参见前引23,严端主编书,第4-16页。
[26]关于英美学界对这一两元模式应用的相关论述可参见 [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7]即使到了1990年代中期,仍有部分教材在一定程度上仍奉行阶级分析方法,如《刑事诉讼法纲要》(崔敏主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版)就继续把对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的介绍放在“剥削阶级国家刑事诉讼制度”一章之中。
[28]徐友军:《比较刑事程序结构》,现代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29]参见前注2,李心鉴书,第85一98页。
[30]前注27,崔敏主编书,第11页。
[31]樊祟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32]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314 - 322页。
[33]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34]程味秋:“两大法系刑事诉讼模式之比较”,《比较法研究》1997年第2期。
[35]左卫民:“实体真实、价值观和诉讼程序”,《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36]前注2,左卫民书。需要进一步交代的是,笔者从1991年起即开始关注职权主义诉讼制度,认为以之界定大陆 法系的基本架构基本成立。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认识到,这种理解有不尽准确甚至错误之处,职权主义只是我们理解欧陆刑事诉讼基本构架的概括性概念,而非现代欧陆模式之本质精神的表述。具体讨论可参见左卫民、万毅:“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左卫民:“实然与应然: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本土构建”,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
[37]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102页。
[38]孙长永:《探索正当程序—比较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版,第441 -453页。
[39]如张建伟在其所著的《刑事诉讼法通义》中并没有提及两大法系刑事诉讼制度的问题,更没有使用职权主义与 当事人主义的概念。他只是整体性地介绍西方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并围绕程序法定主义与实质真实发现主义这两个概念讨论了域外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参见张建伟:《刑事诉讼法通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1-82页、第100-114页。笔者本人在2003年也曾以传统/现代为分析框架,基于两大法系刑事诉讼制度的共同性原理与价值,将之都称为“现代性的刑事诉讼制度”。参见前注36,左卫民、万毅文。
[40]前引2,徐益初文。
[41]参见前引26,达玛什卡书,第160-161页。
[42]前引2,左卫民书,第154页。
[43]田丰乐:“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应实行职权主义当事人化”,《法律科学》1995年第5期。
[44]代表性的论述可参见徐静村:“刑事审判模式之比较与改革”,《现代法学》1994年第6期;谢佑平:“刑事审判模式探析”,《政法论坛》1994年第2期;等等。
[45]板仓松太郎:《刑事诉讼法玄义》,严松堂书店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版,第266-326页。
[46]平沼骐一郎:《新刑事诉讼法要论》,日本大学出版部大正十二年(1923年)版,第88-100页。
[47]牧野英一:《刑事诉讼法》,有斐阁1940年版,第11-13页。
[48]参见前引47,牧野英一书,第9-17页。
[49]参见前引47,牧野英一书,第6-8页。
[50]滝川幸辰编:《刑事法学辞典》(增补版),有斐阁1963年版。
[51] [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52]高田卓尔:《刑事诉讼法》,青林书院新社1978年版,第77页。
[53]转引自铃木茂嗣:《刑事诉讼的基本构造》,成文堂1979年版,第154页。
[54] [日]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诉讼法》(上册),丁相顺译,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从松尾教授的论述来看,他似乎并不愿意运用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来概括刑事诉讼模式。他认为,刑事诉讼一般可以分为实体真实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两个相对的类型。详细论述可参见松尾浩也书,第13-14页。
[55]井户田侃:《刑事手续的构造序说》,有斐閣1971年版,第143-144页。
[56]田宫裕:《刑事诉讼法》(新版),有斐閣1996年版,第12-15页。
[57]从平野教授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其所使用的职权主义的相对概念是“当事人平等主义”和“辩论主义”。参见平野龙一:《诉因和证据》,有斐阁1981年版,第92-93页。
[58]部分日本学者在英美学者的影响下,认为二战前的日本刑事诉讼制度具有“职权主义”的色彩。如团藤重光就 认为战前司法具有“官权主义”色彩(参见团藤重光:《新刑事诉讼法纲要》,创文社版昭和三十三年版,第15-16页);平野龙一也认为德川时代的日本刑事诉讼制度采行纠问式,而大正年间的刑事诉讼则具有职权主义因素(参见平野龙一:《刑事诉讼法》,有斐阁1958年版,第14-15页);井户田侃也说到,日本战败前的刑事诉讼制度带有职权主义的色彩(参见前引55,井户田侃书,第119-144页)。
[59]比如,松尾浩也教授就认为,日本的刑事诉讼制度,经过二战后三个阶段的修改,现在已接近于以正当程序为本位的刑事诉讼法。前引54,松尾浩也书,第14页。
[60]约翰·H·兰本:《比较刑事诉讼:德国》(John H. Langbein, Comparative Criminal Procedure: Germany, West Pub- lishing Company, 1,1977 )。此外还有学者使用与“inquisitorial'’同源的名词“inquisitoriality",但不常用。理查德. K·维格:《世界视野中的刑事司法》(See Richard K. Vogler, A World View of Criminal Justice, Ashgate, 22, 2005)。
[61]这一时间也是法国与欧陆其他国家反思自己的刑事诉讼制度并加以变革的历史性时刻,当时欧陆学界开始细致地体察英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此后英美也开始关注欧陆的刑事诉讼制度,相应的比较研究得以展开,类似的 两分范式也随之流行。参见前引60, Richard K. Vogler书,第45-60页。
[62]杰弗里·雷曼,谢瑞里·菲尔普斯:《美国法韦氏全书》(Jeffrey Lehman & Shirelle Phelps, West's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Law,Gale Cengage,2004)。
[63]参见前注26,达玛什卡书,第4-5页。
[64]阿拉伯罕·葛斯登,马库斯:《三种“纠问制”体系中司法监督的神话:法国,意大利和德国》(Abraham Goldstein &Marcus, The Myth of Judicial Supervision in Three “inquisitorial” Systems: France, Italy, and Germany, 87 YALE LJ.240,1977)。
[65]Spencer认为,不论英美还是欧陆,诉讼的最后阶段都是在公开的法庭上口头进行。不过,欧陆在保释听证和预审等初步程序阶段表现出更强的秘密性。同时,欧陆同样实行严格的无罪推定。但与英美一样,都希望被告为揭示真相提供帮助。麦瑞里·德麦斯一马蒂,J . R·斯宾塞:《欧洲刑事诉讼》(Mireille Delmas-Marty & J. R. Spencer, European Criminal Procedur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4,2002)。
[66]参见前注65, Delmas-Marty&J. R. Spencer编书,第26-27页。
[67]参见前引60, Richard K. Vogler书,第19-20页。
[68]马克西姆·兰格:《辩诉交易的全球化和刑事诉讼的美国化论题》(Maximo Langer, The Globalization of Plea Bar-gaining and the Americanization Thesis in Criminal Procedure, 45 Harv. Intl L. J. 1,8,2004)。
[69]前引26,达玛什卡书,第6页。
[70]前引26,达玛什卡书,第4页。
[71]A·埃斯梅因(约翰·辛普森翻译):《大陆法系刑事诉讼的历史》(A. Esmein john Simpson trans. , 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riminal Procedure, Little Brown&Company,3一12,1913)。
[72]前引26,达玛什卡书,第282页。
[73]前引26,达玛什卡书,第287页。
[74]比如Richard K. Vogler就认为,当代inquisitoriality体现的职业主义、对真相查明的强烈愿望、以及演绎思维确有相当诱惑力,但对其长期历史发展中的残暴性和恐怖性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参见前引60, Richard K. Vogler书,第21页。英美学界这一认识甚至在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都还大有存在。比如在“米兰达案”的判决意见中,首席大法官沃伦就论及,是否以各种手段强迫处于羁押状态的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是当事人主义与“in-quisitorial System”的重要区别之一。See Miranda v. Arizona, 384 U. S. 436, 533 (1966).
[75]转引自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76]如耶鲁大学郎本教授就对德国刑事诉讼制度相当推崇。参见前引60, John H. Langbein书,第1-2页。
[77]前引71 , A. Esmein书,第11-12页。
[78]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刑事诉讼的模式》( Mirjan. R. Danragka, Models of Criminal Procedure, in 51 Zbornik, Collected Papers of Zagreb Law School ,477-516,2001)。
[79]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定罪的证据障碍与刑事诉讼的两种模式》(Mirjan. R. Dama9ka, Evidentiary Barriers to Conviction and Two Models of Criminal Procedure : A Comparative Study ,12 1 U. Pa. L. Rev. 506,1973)。
[80]参见前引26,达玛什卡书。
[81]德国的罗科信、法国的斯特法尼、勒瓦索、布洛克等人均有类似的观点。相关论述分别参见 [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25页; [法]卡斯东·斯特法尼:《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9年版,第65页。另外,即使是倾向用审问式/职权原则来描述德国刑事 诉讼法的魏根特教授,也认为德国的刑事诉讼法是英国普通法与法国大革命后刑事诉讼法的混合物。详细讨 论可参见 [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一6页。
[82]斯特汉·兰思曼:《对抗制:一种描述和防御》(Stephan Landsman, The Adversary System: A Description and Defens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48-51,1984)。
[83]据Wikipedia上的解释,Inquisition一词来源于processus per inquisitionem·
[84]薛建成主编译:《拉鲁斯法汉双解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8页。
[85]关于法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变迁参见前引73, A. Esmein书。
[86]不过,Spencer认为1808年《重罪审理法典》并未回归纠问制,而是建立了一种非对抗、非纠问的“混合制”模式。见前引65, Mireille Delmas-Marty&J. R. Spencer编书,第11页。
[87]前引81,卡斯东·斯特法尼等书,第88页。
[88]前引71,A. Esmein书,第3-12页。
[89]上文提到的斯特法尼等教授就持这种认识。
[90]Berard Bouloc在Procedure penale一书中使用的是accusatoire一词,伯尔尼·波洛克:《刑事诉讼》(Berard Bou-loc. Procedure penale. Paris:Dalloz,p.62,2006)。
[91]参见程味秋:《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简介》,第2页,载《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谢朝华、余叔通译,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1997年版。
[92]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同笔者一样,林钰雄也认为,职权原则”概念在台湾学界被极度误解和滥用,已经无法沟通任何实质内涵。
[93]格雷费斯:《法律词典》(Greifelds , Rechtswoeterbuch,17Auflalge , C. H. Beck Muenchen 2002, S. 1429 )。
[94]该原则集中体现于《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5条第2项及244条第2项。参见前引81,克劳斯·罗科信书,第 114-115页。
[95]前注81,托马斯·魏根特书,第2页。据德国赫尔曼在给笔者的邮件中介绍,Amtsemrittlung表示法官依职权主 动(ex Officio)发现真相,Untersuchungs grundsatz指审判的时候由法官询(讯)问被告人与证人来调查证据,Amt-sermittlungsg undsatz与Untersuch ungsgrundsatz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只是后者更为常用。
[96] [西德]埃贝哈德·斯密特:“西德刑事诉讼程序概述”,周叶谦译,载《法学译丛》1979年第5期。
[97]前注81,克劳斯·罗科信书,第625页。
[98]前注81,托马斯·魏根特书,第1-4页。
[99]参见前引26,达玛什卡书,第147页。
[100] 参见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