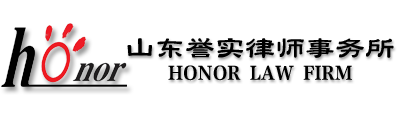在保守的农耕文明中,人们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里,错综复杂的亲情、家族、近邻、乡里关系使人们彼此之间十分熟悉,也易使人们不自觉地联合起来回避司法的过多干预,从而更好地维护原来的人脉关系。
在星光灿烂的历史长河中,古代中国的司法文化曾盛极一时,光彩夺目。虽然西方现代司法文化的传入导致了中国本土司法文化的断流,但“以史为鉴、可以见兴替”。从古代文献中的点点滴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司法文明大观,亦可更全面总结出法律天生的桎梏,难以摆脱的困境。在此,我将以一则传奇的民间司法故事为引,从而表达对法律困境的些许拙见。
据《初刻拍案惊奇》记载:“明朝年间浙江温州府永嘉县有一王生,一日踏春饮酒归来,见一卖姜老翁与家丁争执,王生上前一探究竟,言语几句后,王生怒将老翁推将在地。老翁痰火攻心昏将过去。王生顿时酒醒,将老翁救活后,便连谢不是,讨些酒饭与老翁吃后,又拿出白绢一匹相赠。老翁自渡船回家,王生自以为相安无事。该夜一船家找到王生,言老翁于船中发病死去,老翁死前央其告官索命,并以竹篮和白绢为凭。王生顿时慌乱,欲以金银止祸端,船家得重金后与王生家丁连夜将尸首掩埋于偏僻之所。过了一年光景,王生一家丁胡阿虎由于误事被王生重打,胡阿虎怀恨在心,于官府告发王生年前杀人掩尸一事。官府挖出腐尸并取言于街坊,加以刑讯使王生招供入狱。年过半载,老翁故地重游,上门拜访。王生家人始知此乃冤案一桩。官府最终查明此乃船家借死尸设计诈银。王生无罪出狱,免成冤魂,船家重杖至死,人财两空”。
人性与法
所谓人性,即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法因人而立,依人而行,故法难逃人性的影响。只是更为先进文明的法制将人性的影响尽可能控制在最小限度。船家是本案的罪魁祸首,其利欲熏心,借用一具浮尸,将老翁手中的竹篮和白绢买过来,利用天黑的时机,实施了这桩诈骗案件。这些只是船家计谋的硬件条件,但此案件的软件条件便在于法律的威慑力和人趋利避害的本能。法是用来惩恶扬善的,法是人们寻求正义最重要、最有力的武器。而此时此处法律的威严被船家肮脏的不良动机所利用。法成为了谋取非法利益的工具,这不是与法的初衷背道而驰吗?法固然有自己的价值和独特功能,但法终究免不了工具性的一面。
这种歪曲利用的根源便是人性。家丁胡阿虎虽然有举报犯罪的权利和义务,但他却在遭到王生毒打后才上报官府,我们可明显看出胡阿虎公报私仇的丑恶目的。法律成了其泄私恨的工具。虽然法律不去关注原告的报案动机,但法律威严却常常因此大打折扣。既然人为了牟利、为了私恨而利用法律,那么人们亦可以由于其他层出不穷的欲望和私念去恶意用法。
文化与法
在中国古代,人们的正义观念是相当朴素的,而且具有宿命论、天命性特点。人们相信公平、正义是上天注定。“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举意我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上天必定会秉公执法,从而维系人间稳定的社会秩序。在本则故事中,卖姜老翁的再次突然出现便被看成是上天维系公正的努力。
有意思的是,如果王生果真含冤而去,人们只会将此看作命运使然,是对前世罪孽的弥补,或是为了来生后世积蓄阴德。王生后来考中进士、苦尽甘来,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似乎从轮回转世的长远视角去看,上天也一定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上天的智慧是那样高超,品格是如此完美而不容忍人去怀疑。虽然窦娥为冤屈而指天骂地,但上天后来也为之鸣不平,使窦娥的三个预言全部实现,最终也让窦娥沉冤得雪。正是这种天持正义的文化观念使古代中国的人们很少去利用世间的法去伸张正义,只要尚未触及生存根本,人们情愿忍辱负重。
古代中国产生厌讼文化的一个原因在于,古代法制的严峻和人们对司法不正确的态度。在保守的农耕文明中,人们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里,错综复杂的亲情、家族、近邻、乡里关系使人们彼此之间十分熟悉,也易使人们不自觉地联合起来回避司法的过多干预,从而更好地维护原来的人脉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农村社会的诉讼率远低于城市的原因。王生为了劝说船家帮他逃脱关系,便说道:“你我同是温州人,也须有些乡里之情,何苦为着外人报仇。”胡阿虎在向官府告状时也说:“这尸首实是一年前打死的,因为主仆之情,有所不忍。”而知晓王生与船家达成协议埋尸逃罪的还有其他家丁,他们一起隐藏事实便是熟人文化使然。
三纲五常的传统和男权社会的特征使王生之妻刘氏不可能也没有权利和义务去揭发丈夫的“罪行”,不过,这点已经被“亲亲得相首匿”法律原则所肯定。因此,司法更多的被古代中国文化排斥在日常生活之外。
执法者与法
不管多么完美的法制也需要人去执行,为了防止执法者受到人性、利益、权力、认知等诸多方面影响而歪曲法律,立法便对执法者的思想政治素养、道德水平、知识能力、专业技能做了很高要求。优秀的执法者才能让法制发挥光芒,达到法律预期的功能。在本故事中,处于纠问式诉讼制度下的知县并未能明察秋毫,并没有合理怀疑各项证据,更没有主动对全案进行全面分析和调查。胡阿虎来官府告状之时,知县并未要求胡阿虎提供任何证据便草率立案,派人抓捕王生。尸首挖出来后,知县并不考虑此腐尸的身份认证问题并对王生进行刑讯逼供。胡阿虎和王生为了告状和逃罪而不断向知县上陈理由,知县认为均言之有理,而不去思考案情,更没有形成自己的审讯思路,全依赖当事人双方的辩论之词。在集侦查和审判于一体的司法制度下,知县的行为涉及失职。
刑讯在封建时期是获得口供的重要方法,但知县却将其作为惟一方法,先后对王生、胡阿虎、船家进行了刑讯。虽然刑讯并没有导致屈打成招,但有滥用刑罚、草菅人命之嫌。在对船家的处置上重杖至死过于严厉,船家本是诈骗钱财的罪行,而知县却言辞灼灼的说:“你这没天理的狠贼,你自己贪他银子,便几乎害得他家破人亡。似此诡计凶谋,不知陷害过多少人?我今日也为永嘉县除了一害”。岂不知,知县自己也是酿成冤案的因素之一。如果我们戏剧性地将知县换作狄仁杰、包拯等公正智慧的官吏,或许就不会导致故事中的结果。由此可见,执法者的素质及职务行为直接决定法律的实现程度。
日月交替、沧海桑田,当代中国的法制已经比古代先进完善了许多。但法律与人性本能、社会文化、科学技术、执法主体等诸多要素的争斗和互动仍然要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