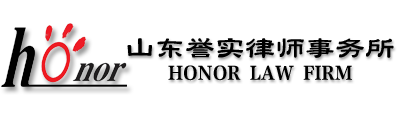基于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反思转型时期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学科分类】法律社会学
【摘要】转型时期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是中西方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然而对这一问题的解说却是远不够深入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一套关于现代社会中法律与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论。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为此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解释,他把系统/环境的区分应用于法律与社会关系的分析,不仅明确了法律作为现代社会之独立功能系统的位置,也阐发了法律与其他社会功能系统之间复杂的互动机制。这一洞见揭示了法律与社会之间共同演化的关系,对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写作年份】2009年
【正文】
一、问题及提出
“法律与社会”是法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尽管对“社会转型”这一概念的界定还存在许多争议,但是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这一观念已被普遍接受,转型不仅意味着社会变迁,而且是一种结构性的变迁,在这种变迁中,法律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不仅更为突出,而且更加地复杂化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深入研究二者的关系,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然而,在当前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不少将二者的关系过于简单化的理论思维。在社会对法律的影响这一问题上,人们常常把法律的变革看作是某个单一社会因素的产品,比如认为“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法治”,认为通过“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就能达到实现法律转型的目的。而即便是认识到法律变革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倾向于在法律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仿佛社会的需求被输入到法律系统当中,法律系统就能生产出相应的法律产品;而在法律对社会的作用问题上,则习惯于把法律当做一种推动社会转型的独立变量,认为有了法律制度就能获得相应的社会效果,从而达致推动社会转型的目的。这些观点的可取之处在于它们注意到了法律与社会之间所存在的联系,但是,对于深入认识二者关系这一目的而言,这样的分析方式并不能真正有效地洞见法律与社会间的复杂关系。从理论上看,这种以目的——手段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理论模型存在许多问题。如果从某个社会领域的角度来理解,我们可以相对明确地区分目的与手段,但是如果从较为一般化的层面观察,则会发现手段与目的是重叠的,它们最终都可以归结到“社会”这一层面,而那种以某个领域为中心的论说方式就会构成悖论:即它自身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在现实当中,目的与手段并不总是能够被清晰地划分开来,因为它们都是在社会中发生的,那些被视为推进社会转型的手段本身也就是社会转型的一部分。此外,我们也会发现这种投入——产出式的分析方式很难对现实情况作有效的解说,比如说法律对社会的作用常常无法完全被预先确定,我们所能掌握的一般只是第一个、直接的效果,却无法控制进一步的效果与副作用,有时候甚至对这种直接效果都难以把握。而法律对社会变迁的回应也并非总是可预见的。
有鉴于此,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尽管法律转型必然受社会转型的影响,法律转型也在影响着社会转型的进程,但是这种在法律与社会之间预设了存在着一种线性因果关系的分析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更为深入的研究的需要,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更为审慎的评估。有的学者已经开始探索一种新的解释方式,比如尹伊君就认为:“对于社会变迁与法律的关系,我所赞成的是一种解释的方法。这一解释的方法将社会变迁看作是一个整体,在整体变迁推移的过程中,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化都与其他部分相关联,因此,任何变化都不能仅靠单一的解释予以说明。法律是社会整体变迁的组成部分,它既是社会变迁的原因,也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同样,社会变迁的其它各种因素也构成法律变迁的原因和结果。它们之间是一种互为解释的关系。” [1]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这种整体性解释如何具体描述二者之间的互动。同时,即便是这种考虑得较为全面的解释,也还是不够充分的,所谓“既是原因又是结果”这样的表述说明他们仍然未能摆脱原因——结果式的思维方式,而这种因果关系存在过于宽泛的可能性,因而很难提供一种有效的解释。
实际上,在当代西方法律研究中,“法与社会变迁”(law and social change)也还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论题,学者们对于法律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推动社会变迁存在着许多截然不同的看法。 [2]而把法律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的“法律与发展运动”(law and development movement)则基本上被证明为是不成功的。 [3]在我看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之所以难以取得突破,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缺乏一套能够真正有效解释法律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一般理论。在传统法律哲学或者说法理学那里,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借用Cotterrell的说法,法律哲学家们倾向于采用一种内部视角来观察法律, [4]无论是自然法学或是实证主义法学,所关注的问题更多的是法律系统自身的规范与效力问题,尽管他们并不必然否定法律与社会的联系,但是更强调法律的自治性。与此同时,虽然法社会学正是把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当作自身研究的主题,并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这一问题,但是,传统法社会学理论从某个社会领域出发来观察法律,不仅不能全面地把握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且容易忽视法律自身的自主性。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传统法社会学理论已经不能适应对不断增加的社会复杂性的把握的要求。
作为二十世纪后半期社会学理论中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意义的解释,他的理论尽管并非针对上述问题而发,但是却能够为我们深入理解此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因此,本文试图在引入卢曼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反思转型时期法律与社会的关系,而这一工作首要的前提就是厘清卢曼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卢曼的法社会学理论较为繁复,为了论述的需要,本文将对其理论的重构分为两个部分,首先重述卢曼关于法律与社会之一般关系的观点,然后着重分析其关于法律与社会的互动理论。最后,在此基础上分析转型时期法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二、社会的法: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界定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传统的法律社会学理论尽管对法律与社会这个问题给予了很多关注,但是并未能够真正有效地解释这一问题。在卢曼看来,不论是马克思、韦伯还是涂尔干,都没有能够解决传统上以部分代替整体的问题,因而所持有的仍然是一种片面的、有限的观点;而埃利希则把法律过度社会化了,以至于模糊了法律与社会之间的边界。 [5]卢曼认为,对于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而言,要处理法律与社会间的复杂关系,应当从系统理论出发,运用系统/环境这一主导性区分(guiding distinct)进行分析。
系统/环境这一区分在一般系统理论中取代了原有的整体/部分的区分。在先前的系统理论中,部分/整体一直是一个主导性的区分,这种将系统视为部分所构成之整体的观念,长久以来主导了对系统进行分析的思维模式。其根本特点在于将整体视作是各部分的总和,而研究的着眼点则集中于部分与整体及部分之间的关系。 [6]这一模式把注意力集中于系统内部,而基本上忽视了系统与其外部的关系,因而被认为不能有效地解释系统持存及运作的实际状态,因为系统实际上是无法离开其环境而存在的。因此,这种把系统视为封闭之构成的观点,逐渐让位于系统与环境关系的研究。
卢曼不仅沿用了一般系统理论的这一重要成果,还进一步阐发了环境对于系统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系统不可能离开环境而存在,系统理论所关注的不应该是系统本身,而应该是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传统理论将复杂系统视为是由‘部分’构成的‘总和’,其基本观点在于总和的秩序说明了孤立的部分永远无法独自拥有的品质。正如我所看到的,最近的系统理论已经通过引入对环境的外部指涉而抛弃了这一传统进路。环境这一概念并不仅仅指存在于所研究的系统之外的事物,这不是一个区分‘这里’和‘其他地方’的问题。这一主题的新颖之处毋宁在于:一个系统的结构和过程只有在与环境的关连中才有可能存在,而且只有在这样的关连中加以考虑才有可能被理解。……甚至我们可以说一个系统就是它与它的环境之间的关连,或者说系统就是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差异。” [7]在卢曼那里,世界是一个总括性的范畴,在这个界域之内,可以观察到诸多的系统,诸如社会系统、心理系统等等,对于这些系统来说,系统之外的一切就构成了其环境。由于在环境中始终存在着比系统内部更多的可能性和偶然性,因此,系统为了维持其存续,需要不断地发展出化约复杂性的机制,而这又导致了环境复杂性的增加,因此卢曼才说只有当关于系统——环境的一种充分复杂性存在时,演化才有可能,而且这个意义上的演化是系统与环境的共同演化。 [8]
在这一理论建构的基础上,卢曼进一步将系统/环境的区分引入社会系统内部,也即将这一区分进行了“再入”(re-entry)。卢曼区分了三种社会分化的形式:区隔分化、阶层分化以及功能分化,这种区分是基于社会型构其次系统的不同原则而做出的。区隔分化形成了平等的次系统,例如家庭或部落;阶层分化则是按照等级高低来划分社会次系统;而功能分化则是依据特定的社会功能,诸如行政管理、经济、教育等等来划分社会次系统。这三种分化形式并非是排他性的,因为即使在最简单的社会中也存在根据年龄和性别的功能分化,而在现代高度复杂的社会中也存在着由家庭、政党等构成的区隔分化。但是,何种分化形式占据主要地位,却是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划分标准。区隔分化和阶层分化对应于复杂性较低的社会形式,而随着社会复杂性的不断增加,功能分化成为了主要的分化形式,这是因为功能分化提高了可能性的过度生产,并且因此增加了选择的机会及压力,由此使得较高的社会复杂性能够在其中得以组织。 [9]只有在社会进入到以功能分化为主的阶段时,独立的社会功能次系统——例如法律系统——才会出现,这些系统都有其特定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因而获得了独立于其他社会领域的自主性。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才能够用系统/环境这一区分来分析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的确,正如拉丁谚语所说:“哪里有社会,哪里就有法律”(ubi societas ibi ius),法律作为社会系统的一种结构,并非现代社会的现象,但是只有在以功能分化为主要形式的现代社会中,法律才成为独立的功能系统。 [10]对于法律的演化而言,卢曼认为对应于主要社会分化形式的变迁,法律经历了古代法、前现代高度文明的法和现代社会的实证法三种形态,前两种法律类型只能适应于相对简单的社会形态,为了应对社会不断增加的复杂性,法律开始逐渐地实证化。实证法的特征在于其可变性,它引入了时间的维度,从而可以更好地处理复杂性问题。与此同时,法律的实证化使得它能够摆脱宗教、道德、政治等因素的直接影响,从而获得了自治。基于这一论断,卢曼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法律与社会之间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
首先,法律是社会中的法律,社会为法律提供了基础并对其构成了限制。法律只有在社会中才是可能的,所有法律系统的运作也是社会的一种沟通,这意味着一方面法律沟通必须符合社会沟通可能性的限制,比如它必须使用正确的语言;另一方面,沟通也是把对实在的社会建构传递到法律当中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由社会通过沟通再生产沟通的网络所支撑的。因此,在把法律与社会视为系统与环境这一关系的基础上,卢曼进一步指出,法律系统是社会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并非仅仅依靠外部资源以获取社会的支持和正当化,而是社会再生产网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1]卢曼反对那种基于 “国家——社会”二分的模式,将法律与社会等同起来,视之为两个单独变量的做法,在他看来,国家是社会中政治系统的一个自我描述,并非外在于社会,而法律也并不必然依赖于国家,相反,只有社会才是法律产生与发展的真正基础。
其次,作为具有特定功能的社会功能次系统,法律对于社会的持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法律本身作为一种限制行为预期的方式,必然存在于每个社会,否则社会中的互动、组织都无法进行。卢曼在其《法社会学》一书的开篇即明确指出:“一切人类的集体生活都是由法律直接或间接地塑造的。法律就像知识一样,是社会情形中一个必要的和无所不在的事实。没有任何一个生活领域——不论是家庭或者宗教共同体,不论是科学研究或者政党的内在关系网——能够找到不立基于法律的稳定的社会秩序。” [12]另一方面,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尽管法律系统的形成乃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但是法律系统的分化出来又成为社会本身分化的结构条件,以及成为诸多其他社会次系统能够分化出来的结构条件。
第三,法律与其他社会功能次系统互为环境。在法律系统分化的同时,社会的其它功能系统,诸如政治、经济、宗教、科学等等也都逐渐形成。这些此系统构成了相互之间环境的一部分。对法律系统来说,政治和经济都属于它环境的一部分,同样,对于政治来说,法律属于它环境的一部分,由是我们需要从一种相互关联的视角出发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即当一个系统的环境发生变动的时候,系统也要相应地变化,然而,对于环境中的系统来说,这一系统的改变也就构成了它们环境的改变,因而它们也要相应地发生改变。它们之间构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互动关系。
三、法律与社会的互动
上面描述了卢曼对法律与社会的基本关系的界定,接下来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作为系统的法律与作为其环境的社会是如何进行互动的。
在系统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从封闭系统理论到开放系统理论再到自创生理论的转变。封闭系统的特色在于它是以内在稳定的方式来维持自己,并且在达致平衡状态之后就不会变化,这样的系统不与其环境保有交换关系。而开放系统论则否定了这种静止的封闭性,在这种理论看来,开放系统可以籍由与其环境的交换过程发展出一种动力,并且能按当时条件而变化其状态,同时又不需随着每次环境条件的改变,而马上完全改变系统的结构。系统与环境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它在环境改变的时候自己调整内部的组织,而不是被外界因果地限制着以及单线地被规定。开放系统理论坚持系统的内部和外在的交互开放,发展的不可逆性及系统对环境的反馈与物质/能量的互换,系统的起始互动与之后衍生的结构之间是不连续的、偶然的,系统与环境处於不间断的输入——转换——输出的循环中。 [13]
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在早期建构在开放系统论的基础之上,然而,他意识到这一理论模型对于现代社会中高度功能分化的状态来说仍然是不充分的,因此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引入了生物学中关于自创生(autopoiesis)的最新理论。这一“范式转换”使卢曼把社会诸系统的统一性和封闭性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这意味着,系统与环境之间不存在投入——产出的联系,而是通过递归的、自我指涉的运作,自己生产和再生产构成自身的要素。对于一个功能系统而言,由于现代社会功能分化所导致的功能特定化,没有哪个功能系统能够解决另一个功能系统的核心问题,因此,这样的功能系统就不可避免地要求自治。
系统的封闭性来源于沟通的封闭性,也就是说,作为系统构成元素的沟通只存在于系统内部,系统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之间都是无法沟通的。每个系统内部的沟通都依凭于不同的二元符码,无论是法律、政治、经济、科学或是道德、宗教,都依据自己的特定功能和符码进行运作。然而,这种运作上的封闭并不意味着系统是与外界隔离的,即它不是指系统在运作过程中不受环境的影响,因为如果没有来自环境的激扰,系统自身的运作就无法继续下去,也就是说,尽管系统是自主的,但它并不是自足的。因此,在封闭的同时,系统也是开放的,它必须对环境保持开放,接受环境中的各种激扰,并通过自身运作化约环境带来的各种复杂性。
具体到对法律系统的分析,合法/非法的二元符码正是确立法律沟通之独特性与自治性的依据,只有能够被识别为合法/非法的沟通才是法律沟通。也就是说,符码是法律系统与其他系统区分的依据,它使得系统能够确定哪些元素属于自身,哪些元素属于环境。进一步的,这种沟通的封闭性体现为规范的封闭性,这意味着“只有法律才能产生法律,只有法律才能改变法律”。与此同时,法律系统也是开放的,它要面对社会中的各种纠纷、冲突或侵害,并被要求在各个社会领域中建立基本的秩序。为了说明这一封闭与开放的同时存在,卢曼引入了规范的预期与认知的预期这一区分,他指出:“法律系统运用这一区分将递归地自我再生产的封闭性和与环境相联系的开放性结合了起来。换言之法律是一个在规范上封闭而在认知上开放的系统。法律系统的自创生在规范上是封闭的,只有法律系统能够授予其元素以法律的规范性,并把它们作为元素建构起来。……这意味着,没有任何具有法律相关性的事件能够从系统的环境那里获得其规范性。在这方面,它仍然依赖于法律元素的自生连接,以及这一连接的限度。同时以及精确地与这种封闭相联系的是,法律系统是一个在认知上开放的系统。……通过程式(programme),它使其自身依赖于事实,并且在事实压力要求时,它也能够改变这一程式。因此,法律中的任何一个运作,信息的每一个法律处理都同时采取了规范和认知取向——同时而且必须连接在一起,但是并不具有同样功能。规范属性服务于系统的自创生,即其在与环境的区分中的自我存续。认知属性则服务于这一过程与系统环境的调和。” [14]符码对于元素如何分配并不能提供明确的指示,而只必须借助程式来完成。在卢曼看来,法律系统的程式乃是一种“条件性程式”(conditional programme),这种程式通过“当A,则B”的形式,来确定法律系统如何分配合法/非法这两个值域,这样一来,就把社会条件引入到了法律沟通当中,在维持自主性的同时也实现了开放性。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系统对环境的感知,即把环境中的事件作为“信息”,并不意味着系统与环境存在着一种信息的交换,也就是说,信息从根本上说也是系统内部自身建构的产物,它并不能穿越系统的边界。系统是通过系统内部对系统/环境这一区分的重新引入而对环境有所感知,从而使系统将这一在系统内部所感知的信息作为运作的依据。因此,系统的开放仍然是一种封闭基础上的开放,它把外在的噪音有选择地识别为信息,并为自身运作所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系统与环境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接触,它们是各自封闭地按照自己的符码和程式进行运作。 [15]系统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这似乎构成了一个悖论,然而对于卢曼来说,系统的封闭恰恰构成了系统开放的基础,开放只有通过封闭才有可能。正如卢曼所指出的:“我们决不是妄自宣称法律可以离开社会,离开个人,离开我们这个星球上特定的物理和化学条件而存在。然而,与这样一种环境的关连只有可能建立在系统内部活动的基础上,通过执行其运作,即只有通过所有这些我们称之为封闭的递归连接而可能。” [16]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封闭,系统存在赖以为凭的统一性就会消失,因而也就不再存在开放与否的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社会功能次系统都是在运作上封闭的,因此,尽管法律与它们互为环境,相互激扰,但是都无法进入对方的运作,也无法成为对方的沟通,那么它们是怎样进行互动的呢?为了阐明这个问题,卢曼采用了“结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这一概念,以指称系统与环境之间不是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系统只能在结构的层次上来处理环境带来的激扰。卢曼认为,结构耦合的概念应当取代投入——产出这一模型,因为它抛弃了那种概莫能外的因果性观念,但同时保留了系统与环境间高度选择性的联系的观念。 [17]结构耦合并非是说信息从系统外部“进入”到了系统内部,它仅仅是意味着一种特定的形式,在这一形式中,系统假定并结构地依赖于其环境中的特定状态或改变。
结构耦合这一概念所针对的,乃是社会功能次系统之间,通过某些特定结构的媒介,使得不同功能系统能够在维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保持较为紧密的联系。结构耦合这个概念为我们理解社会功能系统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基本的分析工具,即它说明了各个功能系统如何在维持自身同一性的前提下回应相互之间的影响。举例来说,法律通过宪法与政治系统形成结构耦合。这是因为在现代宪政国家的理念下,宪法同时扮演了对于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加以限制的结构的角色。虽然宪法作为结构本身是单一的,但是对于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来说,它的意义是不同的,对法律系统而言,宪法构成了法律决定所必须遵守的有效法律文本的最上位法律规范,而对于政治系统而言,宪法则意味着其运作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结构耦合把政治系统的运作转变成对法律系统的激扰,把法律系统的运作转变成对政治系统的激扰,但是又不影响各自的运作的封闭性。 [18]结构耦合与激扰是相互包含的,如果没有结构耦合,就不会有激扰,系统也就没有机会进行学习并改变其结构,因此,卢曼指出,如果没有与社会中其他功能系统的结构耦合这一联系,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就会崩溃。 [19]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初步地了解到卢曼对现代社会中法律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深刻洞见。以系统/环境的关系来分析法律与社会,一方面坚持了法律自身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复杂联系。因此,可以说卢曼的这一理论克服了法律实证主义将法律与社会割裂开的不足,也弥补了传统法律社会学忽视法律自主性的不足。基于这一洞见,卢曼不仅反对把法律与社会割裂开来的做法,也反对那种把法律视为社会控制之工具的观点,而创造了一种虽然更为抽象但是更为全面的分析方式。
四、转型时期的法律与社会
卢曼的上述理论为我们重新认识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架构,他的这一理论揭示了,基于系统与环境这一区分,法律与其他社会功能次系统一样,是一个自我观察、自我指涉、自我再生产的社会功能次系统,但是这种封闭并非隔离,而是通过认知开放和结构耦合从环境中获得激扰,并将其在系统内部有选择性地作为信息加以处理,从而与社会维持一种互动关系。卢曼的这一理论提示了法律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共同演化(co-evolution)的关系,至于它们将向什么方向演化,以及最终达至怎样的状态,则包含了很强的偶然性。本文所试图强调的,也正是“共同”这一含义,即我们应当充分地认识到,法律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实现社会目的的工具,也不能将法律的运作视为是对社会环境的机械回应,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应当进行更深入地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种动态性和复杂性,使得卢曼的这一理论对于分析转型时期的法律与社会之间较为复杂的关系极具启发意义,而这也正是卢曼之前的法律与社会理论所缺乏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已经获得了独立功能的法律系统所起到的绝非是简单的工具作用,它有可能促进了——也有可能阻碍了变革,它有可能适应了——也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忽略了社会变革的要求,它与社会是不可分的,但是他们的运作却又常常不是同步的,它常常被用来规制那些社会生活的新领域,但是却效果各异,立法的大量出现在解决了许多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导致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总而言之,对于这样的情形来说,已经没有一种统一的判准可以作为分析二者间相互关系的依据,而毋宁是这种强调差异、强调复杂性的理论获得了它的优越性。
当然,为了说明的便利,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仍有必要区分开来加以论述。首先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对法律的包容性。这意味着,法律的转型应当被视为是社会转型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于社会的一种独立的变化过程,这一观念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作为社会的功能次系统,法律必然要回应于社会的变革,在社会转型这一背景当中,一方面,许多原有的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因而需要修改;另一方面,则是新的社会领域不断涌现,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来规范。但是,正如上文所强调的,我们不能把法律的这种回应仅仅是做是机械式的过程,以为把社会需要放进法律系统,法律系统就能生产出相应的法律条文。法律系统对于这种环境中变革的反应毋宁是因时因地而不同的,法律系统有一套自己的逻辑来决定何时以及如何做出回应。法律系统对这一信息的处理必须被放到其沟通的操作中,也就是操作的历史中前后相继地加以理解。
法律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问题则更加复杂。社会转型不同于革命,它仍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因此法律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转型提供基本的秩序条件,其次则在于型塑新的社会关系和规则,因为在转型时期各个社会领域的既有规则正在改变,或者新的领域的规则正在形成,而以法律作为这一改变或形成的结构,可以使其被纳入到与整个社会协调的框架中。在卢曼看来,在社会演化的特定历史状态中,功能特定的法律系统之分化出来显现为拥有作为社会演化的成就之特殊的重要性,它是所有进一步社会演化的条件。 [20]然而,那种将法律仅仅视作社会变迁之工具的观念,则是有问题的。在全社会的维度上,作为社会系统的一种结构,法律规范的变化会导致结构的变化,但是,从功能——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结构需要以功能为先导,而不是结构决定功能,因此,如果这一结构的变化并不能起到实现系统功能的作用,那么这一结构就会被其他功能等价物所替代。另一方面,对于社会中的各功能次系统来说,社会系统结构的改变并不必然意味存在着一种因果联系。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系统,政治系统、经济系统以及社会系统之外的意识系统,都是运作封闭的自创生系统,法律的运作并不能决定其他系统的运作,法律提供的实际上是一种选择的可能性,而非一个确定的结果,它只能通过结构耦合对其他功能系统形成激扰。也就是说,虽然这种结构的改变会对整个社会范围内的扰动,因而各个功能系统都要作出回应,但是这种回应是否符合立法本身的意图,则绝非可以预先确定。在许多社会领域中,都存在着他们自己的规则,法律的影响力是有限度的,这与美国法人类学家穆尔在其关于半自治社会领域中法律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21]穆尔的研究可以说为卢曼的法律与社会理论提供了一个实证性的注脚,使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对法律——尤其是立法——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需要更加审慎的评估。
当然,有的法律规则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或者说变革性,有的学者将这种情况的存在作为立法能够有效促进并控制社会变迁的一个例证,比如季卫东转引托克维尔的话认为美国继承法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平等化的社会进程、摧毁了妨碍民主化的地方豪族。 [22]但是我们也马上可以举出相反的例子,比如美国20世纪初实施的禁酒法的失败。 [23]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很难清楚地界分究竟是社会变迁改变了继承法,还是继承法推动了社会变迁。实际上,无论是单独地援引哪个例子,都无法完整地说明法律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因为从系统理论的观点看,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卢曼的这一理论的目的并不在于提供一种确定的指引,当然,人们或许会希望他的理论能够为这一问题提供某些具体的说明,比如说立法者应当怎样制定法律才能更好地实现法律与社会的变迁?但是实际上他对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是存有疑问的。卢曼的理论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规范性论断,如果说他的理论提出了任何具有“应当”成分的观点的话,那毋宁就是要求科学系统中的观察者在认识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仅仅站在某个系统的立场来进行观察,而是应该观察系统是怎样进行观察的,也就是所谓的“二阶观察”(second-order observation)。 [24]现代社会中的功能系统同时也是一个观察系统,它们从自身运作出发观察自身及环境,因此,各个系统对同一个事件或结构的认识都是不同的。我们所选取的观察角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图景,那种仅仅采取内部视角或是外部视角都是不充分的,这样只能观察到法律之内或之外,而无法看到法律与社会这一区分本身。
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卢曼的理论乃是以高度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作为主要关注对象,因此这种分析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社会。中国正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之中,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领域之间尚未实现充分的功能分化,因而还存在着以政治运作代替法律运作的可能性,从而使得分析变得更加的复杂。卢曼就曾指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法律系统尚未真正实现运作封闭并因此抵御来自政治或其他社会领域的直接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就有可能成为政治的符号性工具。 [25]但是,对我们来说卢曼的理论并不因此失去意义,因为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向以功能分化为主的社会分化形式的转变,实际上这也是从所谓“前现代”向“现代”转变的重要特征。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假设,而是对社会实在的观察。因此,虽然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分化尚不充分,但是随着社会复杂性的增加,这种分化的进一步加强是有可能被预见的。由是,运用社会系统理论的系统/环境的区分分析当代中国社会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无疑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正如上文所说,卢曼的这一理论提供了一种观察法律与社会之关系的新的理论模型,我们应当借助于这一新的观察方式,从更为全面的视角来观察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理论与实践提供具有针对性和解释力的理论解说。
【作者简介】
杜健荣,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注释】
[1]尹伊君:《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9页。
[2]比如Dror认为国家以法律为手段组织社会变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参见Yehezkel Dror, 1959.“law and social change”, Tulane Law Review, Vol 33; 而Trubek则认为法只不过是有助于创造社会变迁的条件,并不能直接产生社会变迁,参见David M Trubek, 1972.“Tword a Social Theory of Law: An Essay of the Study of Law and Development”,The Yele Law Journal, Vol 82, No.1.
[3]“法律与发展运动”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批研究拉丁美洲并且视法律为社会变革工具的学者试图输出美国的法律和法学教育,认为有可能发展出一种理论上完备的以法律为核心的发展政策,然而这一尝试很快就失败了。参见James Gardner, 1980. Legal Imperialism: American Lawyers and Foreign Aid in Lat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4]Roger Cotterrell, 2001.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w’s Autonomy in Autopoiesis Theory”, in J Priban and D Nelken (ed), Law’s New Bounderies: The consequences of legal Autopoiesis, Dartmouth: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pp80-103.
[5]Niklas Luhmann, 1999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Law,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pp9-21.
[6]“系统”一词本来是来源于古希腊字sunistemi,意指某个实在各部分因素之集合体,这些因素之间既保持一定的相互关系,又在整体中各自占据自己特定的位置,这代表了传统系统观念的理解模式。参见高宣扬:《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以下。
[7]Niklas Luhmann, 1982.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257.
[8]Niklas Luhmann, 1995. Social Syste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26.
[9]同注 [5], p110.
[10]同注 [7], pp122-137.
[11]Niklas Luhmann, 1992. “Operational Closure and Structural Coupl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Cardozo Law Review, Vol.13, pp1419-1441.
[12]同注 [5], p1.
[13]〔德〕Georg Kneer,Armin Nassehi:《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导引》,鲁贵显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0年版,第26页。关于开放系统理论的更为详尽的论述可参见:〔奥〕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林康义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美〕拉茨洛:《系统哲学引论——一种当代思想的新范式》,钱兆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14]Niklas Luhmann, 1987. “The Unity of Legal System”, in Gunther Teubner(ed), Autopoietic Law-A New approach to Law and Society,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p20.
[15]Niklas Luhmann, 2004. Law as a Social System, Cambri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4.
[16]同注 [15], p105.
[17]同注 [11], pp1419-1441.
[18]同注 [11], pp1419-1441.
[19]同注 [15], p385.
[20]参见汤志杰,1992:“Niklas Luhmann的系统理论及其对对法律的社会学分析”,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238页。
[21]穆尔基于其实证研究的结果指出:“(国家强制实施意义上的)法律仅仅是影响人们所做出的决定、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及其所具有的人际关系的众多因素之一。因而,只有在日常社会生活的环境中来审视法律,那么法律与社会变迁间联系的重要性才会显现出来。在这里,竞争的一般过程(诱导、强制、合作)是有效的行为调节器。起作用的‘游戏规则’包括某些法律和其他十分有效的规范和范例。……许多立法只是零星的,而且只是部分地侵入目前的社会安排。而正是这种零星的立法优势可能显露出社会场景中诸要素的相互依赖或不依赖关系。”〔美〕萨利·穆尔:“法律与社会变迁:以半自治社会领域作为适切的研究主题”,胡昌明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22]季卫东:“社会变迁与法制”,载李楯编:《法律社会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
[23]参见〔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潘大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年版。
[24]关于二阶观察的问题不仅涉及Spencer Brown的形式理论,也涉及Von Foster的二阶控制论,是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相关论述可参见:Niklas Luhmann, 1993.“Deconstruction as Second-Order Observing”,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24, No. 4, Autumn.
[25]同注 [15], p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