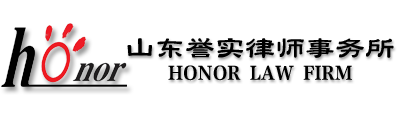案情:某单位职工杨某得知其单位职工工资储蓄存折由财务统一保管,且密码相同后,于2006年9月2日与王某闲谈时提出,弄出几本存折“花花”,王某未作表示。次日,杨某潜入单位财务室,盗出7本存折,并从7个账户内提取现金1.8万元。当日,杨某将此事告知王某,提议将钱花掉,王某表示同意。杨某遂将其中1万元钱交与王某,并称“先花这1万元”。数日内,二人将1万元赃款挥霍一空。
分歧意见:对本案中杨某构成盗窃罪不存异议,但对于王某与杨某共同挥霍赃款的行为如何认定,存在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虽然王某明知是赃款仍予以消费,具有一定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但我国刑法对此类行为没有规定为犯罪,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王某的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与杨某构成盗窃罪的共犯,其挥霍赃款的行为是盗窃的一种后续行为,无需另行定罪。理由是:杨某在盗窃前曾向王某表示欲盗窃存折,事后共同将赃款消费。二人既有盗窃的共谋,也有共同实行行为。第三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评析: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即王某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理由如下:
第一,从侵犯的客体看,王某的行为侵犯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在立法体系上,我国刑法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放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妨害司法罪一节,突出本罪妨害司法罪的性质。因此,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对于犯罪所得赃款,应由司法机关追缴后上缴国库,或退还被害人,这是司法机关的职权所在,属于正常司法活动。本案中,王某将杨盗窃所得的部分赃款与杨某共同消费,导致司法机关无法追缴,或者说追缴成本增大,这无疑是对司法机关正常司法活动的侵犯。
第二,从立法本意看,王某的行为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行为方式。相比较于原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四种传统的行为方式,《刑法修正案(六)》将该罪修改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后,新增加了一个兜底性条款,即“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也就是说,只要能够起到“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作用的行为都符合本罪的行为方式。本案中,王某与杨某共同将赃款消费,客观上起到了“掩饰、隐瞒”的作用,将这一行为理解为“其他掩饰、隐瞒方法”应是合理的。在对原罪名修改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能够起到掩饰、隐瞒作用,但又不明确属于四种传统方式的行为,如收受、抵押等,一些司法机关通常是纳入“窝藏”的范畴。此次修改也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第三,从行为对象上看,赃款应属于“犯罪所得”。有观点认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犯罪对象应限于赃物。笔者认为,此种理解过于片面。实际上,《刑法修正案(六)》在对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修改之前,对于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的犯罪对象是否仅限于赃款确实存有疑义,此次修改初衷之一也在于消除这一疑义,遂将原罪名的“赃物”一词修改为“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赃款当然属于“犯罪所得”。
综上所述,本案中,王某明知是杨某盗窃所得赃款,仍与其共同消费,客观上对杨某的犯罪所得起到了掩饰、隐瞒作用,侵犯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对这一行为以该罪来认定,恰恰体现了对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进行修改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