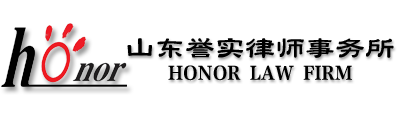许身健博士在《律师以委托人为中心≠“枪手”》中,将委托人决定权上升到“提高人类的自主权和自我控制”的高度。如此立意固然高瞻远瞩,不过,这样的提议还是留着向公权机关去宣讲也许更具宪政意义。人类自主权最大的敌人就是强权和愚昧。
律师的独立职业行为是否就意味着压制乃至剥夺当事人的自主权?首先要注意的是,法律上的自主权和生活中的抉择权是有区别的。一个人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选择何种生活方式,这个由他个人做主;但选择什么样的法律途径,以便更好地实现司法救济目的,这个你得听律师的。委托合同和买卖合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是为维护“别人(合同相对方)的利益”而设置的。自主性的合理行使及适度让渡有助于使委托人理解和接受更有价值的选择及结果,当然,也有法律义务和责任的约束。当事人懵懂之中向泥沼迈进一只脚,律师需要做的是把她拽出来、捞出来,而不是鼓动她继续向前去采撷泥浆上漂浮着的一朵野花!更遑论,时下人们流质善变,一忽儿把律师架空到不切实际的道德高标,一忽儿又对律师坚持内心法则的言行大加挞伐,以及某些法官对律师的动辄指责:“当事人不懂,你律师难道也不明白吗?!”“你是律师吗?!”《检察日报》也曾发出质问:“律师,你为防止冤假错案做了些什么?”就像前几年著名的佘某杀妻案,倘若是因为辩护律师有意替当事人隐瞒某种无罪证据而导致冤案发生,试想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和效应?
我国律师法的有关规定确实隐含某种冲突。一方面,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另一方面,委托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的,律师有权拒绝辩护或者代理。其言外之意就是,律师如果坚持代理而又不向法庭如实陈述,或可视为自愿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后果。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示范规则》则规定了律师对不利于委托人的信息披露的几种特殊情形,原则是不得超过律师合理地认为为实现有关目的所必需的程度,同时规定了律师对裁判庭的坦诚义务,对于可能发生与司法裁判行为有关的欺诈行为,应当采取合理的补救措施,包括必要情况下向裁判庭予以披露,否则可能会与委托人构成共同欺诈。如果所要进行的披露与司法程序有关,其公开的方式应当是把对信息的接触限定在法庭或者其他知道该信息的人的范围内。律师应当尽最大之可能,请求法庭发出适当的保护令或者采取其他措施。这算是一种比较合理有效的回护措施。鉴于不同案件的复杂性,该规则并未将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界定为简单的合同法律关系,而须受其他相关法律及律师职业道德规则的调整,学理上亦将委托关系划分为以委托人意志为重的信托关系模式、需要遵守司法行为规范并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规制模式等多种形态。我国《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中的相关定位也是比较先进的:为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律师有权根据法律的要求和道德的标准,选择完成或实现委托目的的方法。律师应当恪守独立履行职责的原则,不因迎合委托人或满足委托人的不当要求,丧失客观、公正的立场,不得协助委托人实施非法的或具有欺诈性的行为。
律师和当事人之间也会存在某种“拉锯战”和心理对峙,看谁能说服谁,谁能从意志上“控制”另一方(当然,“律师控”可不是“萝莉控”)。有关律师独立性的问题虽然不如其他学术命题那样艰深和晦涩,但往往也只有当事者才能真正体会到或拿捏好其间的分寸和细节。这也牵涉到律师有无独立诉讼权利及法律地位的重大课题。辩护人的权利来源不只是委托人的授权,还有诉讼法律及原则。如律师调查取证不需要委托人的许可,是否举证也可根据实际情况享有一定的自主决定权。此外,律师和检察官同为法律共同体成员,在以平等对抗为精髓的控辩模式中,凭啥检察官就能享有完整的独立性诉讼权利及地位?律师为何就不能拥有必要的超脱和自主?
克罗曼在《迷失的律师》中写道:一端是同情,另一端是超然,做到富有同情心或超然处之都是很难的,前者是一种产生情感的力量,后者则是一种减轻或限制感情的力量,只有运用第二种力量才能节制情感去适应法律程序,而深思熟虑的人特别善于结合这两种力量。在法律的激流和险滩中,律师是把握航向的舵手和摆渡人,他需要冷静的头脑和敏锐的目光,他要为“船客”的安全负责,还要为整条船(包括船上的自己)负责。